東西問丨楊慧林:超越“異邦的想象”看“世界之中國”
中新社北京10月19日電 題:超越“異邦的想象”看“世界之中國”
——專訪中國人民大學原副校長、大華講席教授楊慧林
中新社記者 安英昭

以“構建發展共同體,共創人類新時代”為主題,第二屆通州·全球發展論壇于10月18日至20日在北京舉行。受邀出席論壇的中國人民大學原副校長、大華講席教授楊慧林19日在主題為“多元文明歷程與全球文明發展”的分論壇上與多位外籍學者論道。

“從‘世界之中國’的角度看,我們的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條件破解‘古今中西之爭’。”楊慧林日前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時表示,中西方亟待思想層面的深入對話和雙向闡釋。中西互鑒的對話式研究,應該是超越“異邦的想象”、破解“古今中西之爭”的路徑和前提。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從尼山世界文明論壇到武夷論壇再到此次通州·全球發展論壇,您常與來自不同國家的學者對話,探討文明交流互鑒。不同文明之間為何能實現互鑒?
楊慧林:我們倡導文明互鑒,首先應該思考什么是“互鑒”。互鑒,現在一般英譯為mutual learning,即相互學習。但實際上中文“鑒”字與英文reflection(有反映、反思、表達、沉思、回憶等多重含義)之間有著更有意思的關聯,所謂“互鑒”正是一種相互之間的reflection。在英文中,mutual reflection具有多重涵義(polysemy)及模糊空間(ambiguity),恰與中文“鑒”字的一字多義相似,因而二者亦可互釋。從“互鑒”一詞的中英文互釋即可看出,不同文明之間存在基礎性的共通之處。
實現互鑒的重要前提和方法是比較。中文語境下,《說文解字》言,“二人為從,反從為比”;《漢書》載,“氣同則合,聲比則應”。《廣韻》則解釋“較”為:“與校通,比較也。一人獨校曰校,二人對校曰讎。”這就是漢語本身的內在結構,包含著“相與”而“共在”,而不是“由己”而“求同”的邏輯。這種“對言結構”可見于整個中國傳統。
“相反以見相成”的內容在中國文化典籍中非常多,其思想原型可從《周易》說起,例如《易傳·系辭上》的“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德經》也說“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后相隨,恒也”;在《莊子·秋水》便是“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
西方著名宗教史家米爾恰·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經過詳盡的考察后仍相信,“陰陽消長和相生相成”包含著“中國思想的原創性”。從現代話語方式來看,中國人在講“同”的時候,其實更多是在講“共”。中國人既可以說和而不同,又可以講天下大同;既支持各國保持自身文化特色,又主張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命運與共、美美與共,也是因“相與”而“共在”,并非由“一己”而“求同”。人類命運共同體之“同”并非與“和而不同”相對立,由“共”釋“同”恰恰是中國思想的獨特性。
這就能理解,我們將人類命運共同體譯為“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用“shared future”(側重表“共”意)而非“common destiny”(側重表“同”意)。

中新社記者:您精研比較文學、哲學數十載,從語言文學和哲學思想層面上看,中西方怎樣才能更好地發現并理解對方?
楊慧林:中國和西方之間能夠“發現彼此”,其基本關聯應是在思想、文化層面的“互釋”,既是相互闡釋,也是相互發現。
例如,法國著名詩人謝閣蘭(Victor Segalen)寫的東西可謂“非常中國”,被譽為“法國的中國詩人”。他有一本著作《畫&異域情調論》,其中的論題包括“夏朝的危岌”“商朝的敗亡”“周朝的羞恥”“秦朝的皇陵”“西漢的禪讓”“東漢的狂奔”等,簡直完全是“中國化”。謝閣蘭另外有《異域情調論:一種“多異”的美學》。他把“多異”看成是所有異域的、異常的、意外的、驚異的、神秘的、超人的乃至神圣的,都用“divers”來表達。這里面最關鍵的是體現出“他性”,也就是歐陸哲學的“otherness”或“alterity”。有趣的是,中國文化經常被法國人看成是“多樣性”的坐標,中國和以法國為代表的西方往往互為“異邦的想象”。
中國和西方的政治制度、經濟模式都有所不同,其背后則是理解世界的不同方式。中國與西方交往過程中,我們常說有“三大支柱”——經貿、政治、文化,實際上以法國為例,中法之間最開始并不是商貿往來,而是文化之間的相互認識、溝通乃至欣賞,這種真正深層次的溝通非常重要。
中國與西方許多國家之間都有高級別人文交流機制,以文化活動為推手,以學術交流為依托,以“東西互鑒”“達己達人”為進路,也取得了重要成效。當前背景下,中西方亟待思想層面的深入對話和雙向闡釋,從而才能為中國自身的全面發展和升級轉型提供有利的輿論環境,為當今世界的緊張關系和利益格局輸入必要的平衡機制,為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重要的建設性作用奠定持久的長效基礎。

中新社記者:在“世界之中國”的今天,我們應如何超越“異邦的想象”、破解“古今中西之爭”?
楊慧林:按照法國歷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的說法,“沒有法國史,只有歐洲史;……沒有歐洲史,只有世界史。”梁啟超則在《中國史敘論》中將黃帝至秦代的“上世”稱為“中國之中國”,秦始皇統一中國至清代乾隆末年的“中世”為“亞洲之中國”,“與西人交涉競爭”的“近世”則是“世界之中國”。
從“世界之中國”的角度看,我們的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條件破解“古今中西之爭”,而中西互鑒的對話式研究,應該是超越“異邦的想象”、破解“古今中西之爭”的路徑和前提。正如著名西方宗教研究學者麥克斯·繆勒(Max Müller)在其名作《宗教學導論》中所言,“所有的高深知識都是通過比較獲得的,并且是以比較為基礎。”文明互鑒也需要在對話和比較的方法下進行。

法國巴黎高等師范學院米歇爾·埃斯巴涅(Michel Espagne)教授和我有過多次對話。他曾公開表示,“當今世界越是充滿沖突和誤解,就越是需要學術層面的對話,只有‘對話式’的學術研究才能幫助人類達成真正的相互理解。”我非常贊賞他的看法。
我們主張的“文化自信”,也必然取道于不同文化之間的對話。通過文明對話,你會發現,如果沒有對話,不僅是我們不了解別人,可能對自己也不夠了解。對話不僅是自我表達,也是在比較中自我辨識;不僅是讓他人理解我們,也是使我們更好地理解自己。對話式的研究既是在比較中重述中華文明的獨特肌理,也是針對西方話語的敘述模式;既啟發了重訪自身傳統的機緣,也為“進入”西方知識系統提供了可能。
事實上,中國現代學術本身就是中西對話的產物。例如呂思勉認為,世界上并無真正相同的事情,“所謂相同,都是察之不精,誤以不同之事為同罷了”,但是“各別的文化,其中仍有共同的原理存”,所以“欲了解中國史,固非兼通外國史不行”。錢穆也表示,“最近學者,轉治西人哲學,反以證說古籍,而子學遂大白。……余杭章炳麟,以佛理及西說闡發諸子,……績溪胡適、新會梁啟超繼之,而子學遂風靡一世。”
馮友蘭更在其用英文出版的《中國哲學簡史》中“以西釋中”,不僅從孟德斯鳩式的“地理環境”說明“普天之下”和“四海之內”,以釋“中國文明、特別是中國哲學何以為然”,還將儒家“內圣外王”(inner sage and outer king)比之于柏拉圖的“哲學之王”(philosopher-king),將“反者道之動”(Reversal is the movement of the Tao)比之于黑格爾“一切都包含著對自身的否定”(Everything involves its own negation)。他認為,任何一種哲學都包含著“恒久的”(permanent)的觀念,也包含著“可變的”(changeable)和“共同的”(in common)因素;因此不僅差異之間可以比較,而且可以“用彼方的概念(in terms of the other)予以翻譯”。
正如英國詩人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有一首詩《天真的預言》(Auguries of Innocence),徐志摩、田漢等人曾多次將其譯成中文,措辭卻基本一樣:“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這一相似的翻譯深深地刻在中國人的理解結構之中,因為“一花一世界,一葉一菩提”式的表達在《梵網經》《法華經》等佛教典籍中隨處可見。這也許是“異邦的想象”,但最后達成了多樣性的互釋。(完)
受訪者簡介:

楊慧林,文學碩士、哲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大華講席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原副校長。先后擔任過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中國宗教學會副會長、國際比較文學學會副主席等,主要從事比較文學和宗教學研究。近年出版的主要著作有《意義》(2018修訂版)、《神學詮釋學》(2018增訂版)等,以及英文論文集Christianity, China and the Question of Culture(2014)。

東西問精選:
- 2024年10月21日 17:52:32
- 2024年10月20日 19:41:42
- 2024年10月10日 20:49:43
- 2024年10月07日 20:55:49
- 2024年10月04日 19:06:20
- 2024年10月03日 18:48:21
- 2024年09月30日 20:42:05
- 2024年09月29日 20:38:27
- 2024年09月27日 21:58:25
- 2024年10月21日 22:10: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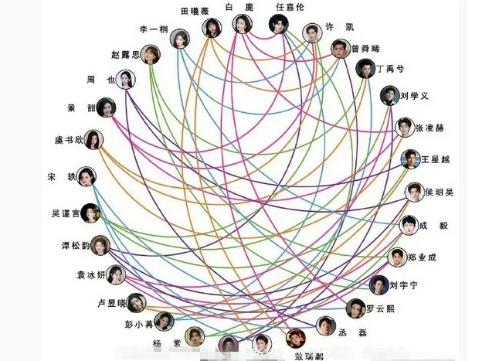









































 京公網安備 11010202009201號
京公網安備 1101020200920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