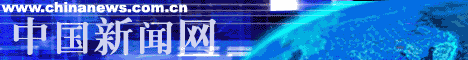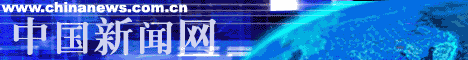(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并注明摘自中國新聞社中國《新聞周刊》。聯系電話:68994602)
發生在遙遠的中東的海灣戰爭,13年前直接傷害到了一些中國公民,他們傷痛不但存在至今,而且還在加深
“還有比我更慘的人嗎?還有比我們這個群體更痛苦的嗎?對于戰爭,我們的體會是切膚之痛,13年了。”孫渤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2003年1月4日,大雪把膠東半島的煙臺裝扮得干凈異常,使之成為一望無際的白色世界。
“而我卻是臟的,由于受到貧鈾彈的核輻射,以及在海灣戰爭中受到的其他現在也不知道名稱的武器的侵害,我已經不是正常人了,我的染色體已經有了變異,我的身體也越來越差了。當時和我一起在海灣地區工作的其他中國人,也都有類似的病狀。現在我們經常聯系,互相鼓勵,繼續活著。”孫渤說。
海灣遺夢
孫渤發表過一部10萬字的書稿——《海灣遺夢》。孫渤是真把他的夢留在了海灣,根本不曾想到自己的一生已經被那場戰爭完全摧毀了。
1989年7月,孫渤到中國駐科威特大使館工作,此后隨著該地區的戰事變化,輾轉其他國家,在聯合國尚未宣布海灣戰爭正式停火之際,于1991年3月又被緊急調往科威特參加被毀的中國使館重建工作,成為首批重返科威特的6名中國外交官之一。此后在那里工作到了1992年2月。
外經貿部人事司1995年9月26日出具證明信,上面寫著:孫渤為我駐科威特人員的緊急撤離做了許多工作,為保證國家和駐科人員的財產不受損失盡職盡責,不辭勞苦,完成了國家交給的各項任務。在艱苦的條件下,為恢復和發展中科經貿關系做出了努力,完成了各項工作任務。
他冒著生命危險,在戰火仍然頻繁燃起、炸彈就在身邊爆炸、地雷密布的環境下搜集材料,曾被伊拉克士兵武裝扣押;后又幫助240多名中建公司的中國人及時安全地撤離……
正是這些行動,將孫渤完全暴露在核輻射下。孫渤是當時在科威特工作的中國人員中清理戰場、搜集材料最多的一個,這也使他成了有相關病兆的群體中最為嚴重的一個。一個生龍活虎的小伙子,現在變成了一刻也離不開治療的病夫。
當時在海灣地區的新華社記者江亞平有同樣的病痛:“雖然我的問題沒有孫渤那么嚴重,但同樣在回國后逐漸出現了影響我的健康的相關病兆。”
另外兩位記者唐師曾、王繼雨則稱自己幸運:“現在的情況還沒有那么嚴重。”
痛苦的生存
染色體嚴重變異,身體的免疫系統、神經系統、內分泌系統、呼吸系統、生殖系統等方面遭到了嚴重破壞——中國協和醫院、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院及為中國主要領導人看病的醫學權威王綿之等機構和個人,均為孫渤作出了類似的診斷。
江亞平則全身肌肉、骨頭劇痛,“疼的時候,我就跪在地上磨自己的膝蓋。”他說。攝影記者唐師曾現在的身體免疫力極低,已經影響到他正常的野外拍攝工作。
當時新華社駐海灣地區首席記者丁文,及當時的駐科威特大使館武官曹彭嶺,現在均患癌癥。
“你說,我還是個人嗎?”講述完自己的病情后,孫渤反問道。
從1997年開始,孫渤不分時間地點,嘔吐加劇,呼吸困難。面對記者,他幾乎說一句話就停下,深呼吸后才能繼續。他情緒不穩定。“我經常有管不住自己的時候,甚至還會打自己的耳光,反正也感覺不到疼。”孫渤說。
與記憶力嚴重衰退的孫渤進行對話是困難的,他自己也承認:“我幾乎記不住在說什么。”從破舊的沙發里起來,對他就像干一場重體力活。
“我們這些人回來后,均有不適,后來發現我們的癥狀竟都一樣,再后來,看到美國的一些關于患有海灣戰爭綜合癥老兵的報道,才知道,我們得的就是海灣戰爭綜合癥。得出這么個結論,我們都感到非常害怕。”
“1991年4月,重返科威特后的一個月,我身體開始感到嚴重不適,胸悶、咳嗽、嘔吐、頭部劇烈疼痛、控制不住情緒。隨后,這種不適加劇。我1986年以優異的文化課成績和四年全優的體育成績從上海對外貿易學院畢業,是我們那一年級僅有的四個有這樣體育成績的畢業生之一,身體強壯,但現在,成了治不了的病秧子。”孫渤不想回憶當時戰場上的經歷,說到那段往事簡單帶過。
“任何響一點的聲音,都會把我帶回硝煙彌漫的戰場,就像做惡夢一樣。你根本理解不了那種煎熬。與其這樣,我寧愿當時在海灣地區被一槍打死或被炸死,現在這種生活漫長而沒有終點,折磨更大。我在那之前也取得了很多成績,但在我就要走向事業輝煌的時候,一場戰爭把我毀了。”孫渤說。
他還有過在火車上聽到大一點的響聲,被驚醒并翻下臥鋪崴傷腳的經歷。“在夢中的那一剎那,以為自己正在戰場上。”
孫渤的父親現在患小腦萎縮,母親眼睛哭得幾乎已經看不到東西,不能生育、婚姻也于前年破裂的孫渤不但不能盡人子之孝,還讓父母操心。。
“上不能孝敬父母,下斷子絕孫,中年又孤身一人,這是戰爭對我造成的最大傷害。”孫渤說到自己不能享受一個人最根本的天倫之樂時,情緒開始更大波動,“我原來認為自己日后還會有更好的發展,但現在,為了治療而變賣家產,已經家徒四壁了。落差太大了。”
“我現在已經不能從事正常人的工作了,精神上沒有任何支撐,”說到這里,孫渤猶豫了一下,“我的性功能已經完全喪失。我也是個人呀,但是現在我在物質上、精神上已經得不到任何享受了。”
這一點,正是江亞平、王繼雨、唐師曾對孫渤最同情之處。“他的確什么享受都沒有了。”江亞平說。
“美國的海灣老兵現在正在爭取去伊拉克,不是去打仗,而是去阻止戰爭的發生,因為他們知道戰爭的殘酷,平常人是很難有這種認識的。”孫渤說。
曾經的精神寄托
有一段時間,孫渤找到了新的精神寄托。
因為身體原因,孫渤從外交崗位被調回家鄉煙臺,邊工作邊休養。
2001年3月一起和孫渤到中國軍事醫學科學院做檢查的幾個人,包括唐師曾,都承認,隨著病情的逐步加劇,原來做的工作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
1993年調入煙臺大學后,孫渤在身體條件允許的情況下,一周授課28節,曾經是該校外語系授課最多的人。
“我拼命工作,就能暫時忘記病痛,而且還可以做出貢獻。最初我還能站著講課,后來坐著。有時候我就在課堂上吐血,但有同學們的理解,我也覺得值。”
一直到去年,孫渤還是帶著一身的病痛努力工作。在他來任教之前,煙臺大學建校8年只有1個人考入孫渤的母校上海對外貿易大學就讀研究生,而孫渤在四年的時間就帶出了10個考入其母校的研究生。
他的學生高潤恒去年7月被清華大學錄取,現已開始博士研究生學習。孫渤還向中國《新聞周刊》展示了這位同學的來信。此外,雖然自己經濟拮據,但孫渤仍然資助他的學生張克偉2000元錢,令其度過學習的難關。
“我8年做了18年的工作,這是校方給我的評價。”孫渤說到了自己的成績,露出了難得一見、飽含成就感的笑容。
對工作狂最大的摧殘,莫過于讓他喪失工作的權利。孫渤現在已經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了,這種基于成績帶來的精神寄托隨之破滅。
相對于孫渤,其他幾個人還好。
“我還好,不管怎么說還能做具體的工作,疼痛還是能忍的。”江亞平說,“但給我按摩的盲人醫師曾經和我說過,沒見過背部肌肉硬得像一塊鐵板的,這種情況,說不影響具體工作也是假的。但我比孫渤要好,他現在什么也不能做,精神上很空虛。”
唐師曾則明確表示,由于身體情況已經不像以前那樣,所以現在很少有機會去自己想去的地方采訪了。
“現在知道孫老師的人是越來越少了,”煙臺大學外語系大二學生何長彪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了他的擔心,“我只是通過幫助孫老師復印一些材料才知道他的經歷,孫老師自己很少和我們說起自己。我現在擔心的是,以后的同學來了,不知道孫老師,連幫助他做點事的人都沒有了。孫老師太苦了。”
身體的價值
“惟一支撐我的,就是我感覺我現在這個身體還有價值。我現在的精神還不錯,就是因為這個認識在支撐著我。”孫渤一直想把自己的身體無償獻給相關的醫療研究部門,他甚至怕等不到那一天,現在已經想好了遺體捐獻的事情了。
孫渤不能擁有一個正常人所擁有的夢,現在的一個不“正常”的夢想,能不能實現?
孫渤的新夢就是把自己變成實驗品:“在中國,我們這些飽受現代武器侵害的人不多,然而,這個群體卻有巨大的研究價值。如果能通過研究我們這個群體,得到緩解甚至找到救治‘海灣戰爭綜合癥’的方法,那在戰略上的價值得有多大?”
“但是我輾轉了很多醫院、醫療研究機構,都沒能實現我的夢想。我身體這么多年的變化,是多么珍貴的一筆數據,但現在,一點系統的記錄也沒有。如果就這么死了,一點價值也沒有了。我們這個群體對于對治療這種病是有價值的,存在價值卻被忽視了!”
“王綿之老先生曾經表示,不要漠視我們這個群體出現的新病狀,要新事新辦,如果漠視,就是失職。在海灣戰爭中有80%的武器是首次使用的,需要我們國家就此作出研究。但遺憾的是,到現在,我們這個群體仍然沒有得到相關部門的重視,甚至在我們治病的過程中,還有一個高級研究部門的領導人說我們沒病,不要往‘海灣戰爭綜合癥’上靠了,好像我們這個群體在利用這種病,我們感到無比的氣憤!我們有很多病歷,上面都有非常專業的診斷結果,怎么還會有人這么說呢?我們在海灣地區的時候就有很明顯的反應了,難道還要回到中國后才裝病嗎?”孫渤對他求醫路上曾經遭受到的誤解一直憤憤不平。
江亞平則說,“2001年3月我們一起在北京治療時,孫渤就向中國軍事醫學科學院表示了他這個想法,2001年3月,中國軍事醫學科學院給我們這些在海灣戰爭后身體有明顯變化的人——我、孫渤、丁文、曹彭嶺及王繼雨,做了一次免費的體檢,有一個結果很能說明問題:我們五個人全部是染色體變異。染色體變異在普通人中只有千分之二發生率。五個人中丁文和曹彭嶺還身患癌癥。專家都清楚我有病,但都不能確診是什么病。正是因為不能確診,我們這個群體才有被研究的價值,這也是王綿之老先生的觀點。”
“我以前壯如牛,現在卻被感冒害得冬天不敢出門。在1995年曾大病一場,就是由感冒引起的,雖然和我以前的體質比很不正常,但還沒太注意。1998年,北大醫院抽了我的骨髓化驗,確定為再生障礙性貧血。現在的身體抵抗能力已經很弱了,很容易得重感冒、肺炎、肝炎等,身體發生這么巨大的變化,和我當時在海灣地區的經歷有關。”
“我比孫渤幸運多了,我現在恢復得不錯,不會影響我的具體工作。但孫渤的這種想法很有價值,雖然我們這個群體很小,但的確值得專門進行研究。對待這種現代戰爭中出現的新情況,應該有前瞻性的眼光。”王繼雨說。
阿富汗去年也受到貧鈾彈的打擊,貧鈾彈的危害就發生在中國的鄰國。再有,現在國際恐怖主義肆行,提前研究我們這個群體,也是目前反恐的一個重要課題。誰能說恐怖主義分子就不會使用類似武器呢?孫渤的夢想如果能夠實現的話,那就是辦了一件好事,一件偉大的事情,對中國前瞻性地介入這個領域的研究有重大的意義。王繼雨解釋道。
孫渤:再赴海灣
孫渤現在正在等簽證,他要自費去科威特治療,同時也是身體力行宣揚和平。
“中東地區的一些國家,還有美國,對海灣戰爭綜合癥的治療很有心得,但不公開。如果能把我及我們這個群體當作實驗對象的話,我覺得我們國家也會在海灣戰爭綜合癥上有突破。這個想法2001年3月被拒絕后,我還一直還主動和很多研究機構聯系過,但仍然沒有任何回應。也有很多朋友正在幫我聯系,都希望我的這個想法實現。”孫渤說。
“對個體關注我是個突破,中央領導、山東省委領導都對我的事做過特別批示,我非常感謝。指示明確,但落實方面,我是著急的,我現在一直在等那些指示更好地執行。2001年的11月18號就有了批示,但我希望能執行得再快一點。”
“我也想活命,想好好活著,但現在這種根本就沒有確診的常規性治療,我感覺我就是在等死,而且等得沒有任何價值。如果能有系統的研究,說不定中國對海灣戰爭綜合癥的治療有突破的時候,我也會得到延續生命的機會。”
“很簡單,我想活著,想做事情。”孫渤說。
文章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原標題:被海灣戰爭傷害的中國人
作者:馬韜 姜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