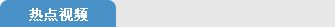- 飛行員是這樣煉成的? 會飛之前要先學會跳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這是一個身上混合著夢幻與傳奇的、讓人艷羨的群體。義無反顧地投身其中,也是源于對這個群體的強烈渴望。
接下來的故事,就不那么浪漫迷人了。嚴苛的選拔,“與死神擦肩”一般的苦練,跳傘的新奇與恐懼,學習飛行的慌亂,是他們相繼要面對的。而與這個職業不可分割的,還有苦行僧般的生活,以及身體承受的巨大損耗
本刊記者/張蕾(發自北京、河北) 張鷺(發自吉林)
拓坤每周至少跟家里通一次電話,電話的最主要內容是報告自己平安。家人最常叮囑的是:開飛機一定要小心,開慢一點。
拓坤每次都要糾正:開飛機又不是開車,其實越慢越不安全。
這樣的對話經常發生在他剛開始學飛行的時候。
“我來學飛行家里覺得挺光榮的,但也還是挺擔心。”拓坤說。
他是河北某飛行學院高級教練機團的學員。
如果一切按照他的想象,未來,拓坤將駕駛我軍戰斗機,“一直飛下去”。
“藍天在召喚”
一年半以前,原本在武漢海軍工程大學就讀的拓坤聽說空軍在招大學生飛行學員,決定報考。
空軍招飛的宣傳簡章上,最醒目的是五個描紅的大字:藍天在召喚。
“飛行員政治地位高,榮譽高,是崇高的職業。人家都羨慕。”拓坤說,他其實很喜歡大海,喜歡海軍,遺憾的是“不能飛行”。
在高教團,跟拓坤同屆的路虎云、李長霖是陸軍學院出身,他們來空軍也想進行“不同的嘗試”。
在位于吉林的空軍航空大學,另一群年輕人也有著相似的經歷。
2008年5月,面對考官“為什么想當空軍”的提問,鄭福明的答案簡單到貧乏,“就是從小想當”。對天空難以名狀的憧憬,讓鄭福明一直渴望招飛的機會。高考那年,他所在省份并沒有招飛計劃,鄭福明選擇了一條曲線道路,他以599分的高分填報了民航大學空中交通管制專業,其與飛行專業在課程設置上相似,大致的區別在于,前者不學飛行。
出生于軍人家庭的郝宇加入空軍則更像是傳承家族血統——爺爺是高炮部隊的老兵,所在的營還曾打下過美軍的飛機,活捉跳傘的飛行員;父親曾在某部隊雷達班服役。
大二那年,在空軍招飛網上,一直搜集相關信息的鄭福明看到了招飛的消息。機會源于空軍選拔飛行員的新政策。2006年開始,空軍招飛局在全國178所普通高校理工類本科二年級男生中試點選拔飛行學員,進入空軍飛行院校學習兩年,也就是俗稱的“2+2”體制。
據說,那一年最初參與競爭的有四五萬人。
傳說中的空軍招飛體檢,苛刻到可怕。空軍招飛局北京選拔中心計劃科科長朱青海覺得,外界對空軍飛行學員的體檢標準存在誤解,像網上傳說的“青春痘”“少白頭”都會被剝奪招飛資格,朱青海認為這并不屬實。
關于對耳洞的限定,朱青海也做了解釋:“一個男孩子將來要是成為首長了,耳朵上帶個耳洞⋯⋯這個形象不好,同等條件下我們就要考慮(將其淘汰)。但如果不太明顯,慢慢能長上,那影響不大。孩子十七八歲,什么想法都有,應該允許他們有想法。”
同年闖過苛刻體檢關的拓坤、路虎云、邱海峰等人的理解是:“我們那時,有耳洞肯定是不行的。”
邱海峰連耳壓都差點沒過關。體檢中一個環節是捏著鼻子鼓氣,耳膜要鼓起來,就說明耳壓符合要求。當時邱海峰憋了半天,右耳膜也沒鼓起來。吃完晚飯,七八點鐘回到宿舍,別人打牌放松,邱海峰自己在一旁練習鼓氣,一直練到12點鐘。
“聽到耳朵里有響,我知道鼓起來了。”邱海峰說。
除了身高、血壓、內臟功能的嚴格限制,在針對飛行員而設計的特殊檢測中,電動轉椅是最令人發怵的項目。在轉椅轉動時,自己還得不停地晃頭,這樣身體的轉動就有了兩個軸心,2秒一圈的速度轉下來,要站穩已經十分困難。而在面對檢測心理品質的飛行模擬器時,他們需要在保持飛機平衡的前提下,記住耳機里報出的數字和屏幕上不斷涌現的圖形。
體檢是進入空軍飛行學員的第一道關卡,也是為公眾所知的最無情的一道,80%的人倒在預選、初選的體檢上;在進一步的全面檢測中,身體檢查有129個大項,1000多個小項,心理品質測試還有三道大關。種種檢查,其標準就是“看你是否適合飛行的環境”。
從2009年開始,空軍招飛的視力標準從環形表1.0(即“C”字型視力表,環形表1.0相當于E字表的1.2——編者注)下調至0.8,這是空軍招飛體檢標準建立以來改動最大的一項,原因是空軍正在分機種招收飛行學員。
據朱青海介紹,隨著空軍招飛的文化水平要求逐年提高(兩年里對高考的分數要求提高了近100分,在招收大學生飛行員時則要求其當年高考分數達到本省的普通二本線),身體標準有所下調。這是因為,隨著飛行科技的發展,有賴于先進的儀表,“靠目測的東西越來越少。”
經過一個星期的滾動體檢,拓坤和邱海峰發現,兩輛大巴車拉去的海軍工程學院的同學,只剩下8個。而最終走上飛機的,只有3個。
相對于更加嚴酷的飛行訓練,體檢顯然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按飛行學員李新咚的話說,體檢過關,“只是說明你可以站在起跑線而已”。
我國實施高溫補貼政策已有年頭了,但是多地標準已數年未漲,高溫津貼落實遭遇尷尬。
Copyright ©1999-2024 chinanews.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