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mlr8.com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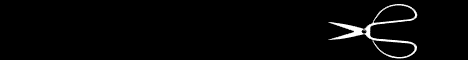 |
|
沈寧深情憶夏衍 文.祝曉風
北京音樂廳旁邊的大六部口街十四號沈宅。夏衍在這里度過了他一生中最后的時光,他九十五年生命的傳奇就是在這里結束的,這個院子留下了這位老人最后的夢想。 沈寧和旦華 夏衍曾經用過“沈寧”、“黃子布”、“丁謙平”等名字在二、三十年代翻譯了蘇聯電影攝制臺本《生路》、電影藝術理論《時間的特寫》、撰寫了電影評論文章《蘇聯電影十七年》等,是最早向中國介紹蘇聯電影的翻譯家之一。沈寧說,夏衍用“沈寧”這個名字就是因為女兒的緣故。沈寧說,當年在重慶、上海,父親每天做地下工作,名字經常換,她也不知道父親每天具體干些什么,他當然也不說。也因為當年父親做地下工作,所以很少照相。 這張照片是1932年,夏衍、蔡淑馨和他們的女兒的合影,是老照片中很少的沈寧和父母的合影。那時,父母都正值壯年,沈寧也還是一個天真的兒童。如今,照片上風華正茂的那對伴侶都已走了,照片上那個可愛的孩子,也已是一位平和、慈祥的老人了。 沈寧是夏衍的長女,今年已年近古稀,她還有一個弟弟旦華。沈寧是在上海讀的中學,后來在香港入“新青”,解放前入了華北大學,所以算解放前參軍。后來華北大學改為中國人民大學,沈寧本來想讀外語,結果卻讀了政治經濟學,后來還上了研究生,畢業之后就留校了。1954年,她被派往蘇聯,繼續念經濟學,1960年初回北京,到中國社科院《世界文學》編輯部工作。六十年代,她曾為《世界文學》設計過封面。 “文革”中,因為夏衍的關系,沈寧也受到過嚴厲的盤問,但并沒有遭到嚴重的沖擊。她現在還記得當時被審查時要回答的“很奇怪的問題”──那些人問她,“解放前你父親有沒有被捕過?”“夏衍有沒有晚上不回家的時候?”──“這些問題我當時都覺得很奇怪,不知道該怎么回答。”
“文革”后,沈寧又回到《世界文學》,她退休前則在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做翻譯和編輯工作。夏衍晚年一直和沈寧、旦華兩家人住在一起。沈寧說,父親還是老輩人的觀念,愿意一大家子住在一起。 夏公愛貓是出名的,可夏公并不是什么貓都喜歡,他只喜歡黃貓。沈寧說,那時他們家的貓是最自由的,每天屋里屋外、房上房下地跑。 旦華是學理科的。1975年,夏衍剛剛出獄時,旦華曾代表父親向夏衍的老朋友吳祖光通報消息。這次采訪不巧,沒有見到旦華先生。沈寧和旦華也各有一兒一女,像他們自己和他們的父母一樣。 方桌和皮鞋 屋子正中的這張方桌看上去有些舊了,沈寧說,這是她在六十年代初買的。“文革”當中,有一次他們家被抄,房間幾乎都已被封了。那天快到用飯的時候,父親夏衍從屋中搬出這張桌子,說“你們可以用這張桌子吃飯”,那神態從容平靜。沈寧說,父親是老革命,老地下黨,從這件事就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很鎮靜的人。他經歷過那么多風雨坎坷,見過那么多大世面,遇到過那么多危險,確實能做到臨危不亂。 沈寧給我們看夏衍的舊物。她說,這是父親生前穿過的皮鞋。這雙鞋的一只右鞋底比左鞋底高出許多。兩只鞋底不一樣,是因為“文革”中,夏衍在監獄中落下終生殘疾。 1966年夏天,夏衍被游街示眾。紅衛兵用鞭子逼著夏衍唱“我有罪、我有罪”。夏衍實在唱不出口,便遭到了毒打。北京電影制片廠廠長汪洋曾寫過文章回憶過這一段經歷,他說,那一年八、九月間,他和夏衍被關在食堂門口一個小木房子里等著輪流批斗,夏公“可憐得連煙都沒得抽。我把口袋里藏著的大半包煙,偷偷給了他”。 1966年12月,夏衍被抓起來關押在北京衛戍區,后又轉到秦城監獄,開始了長達八年零七個月之久的“監護”生活。“曾長期在敵人的眼皮底下出生入死地為黨和人民辛勤工作,巧妙地躲避了敵人一次又一次的追捕,從未經歷過鐵窗生涯的夏衍,卻在新中國誕生后的十七年,被關進了”“無產階級專政的牢房。”(周斌:《夏衍傳略》)“他那本來很健康的右腿,也是在獄中被踢打而致殘的。令人發指的是,這些造反派把夏衍的腿打成骨折,竟連醫院都不送,而是任其自行愈合,以致落下了終生的殘疾。”(會林、紹武:《夏衍傳》)沈寧說,當年父親在獄中受了不少罪,那時每天上廁所都有時間限制,誰走得慢了看守就會在后面叫,有時還會踢打,對夏衍這位當時年已七十的老人也不例外。林彪垮臺后,夏衍可以和家屬見面了。沈寧現在還記得那一次見面的情景。因為和家屬會面時都有看守在一旁監視,所以見了面夏衍也不能和家人多說什么,但他卻偷偷塞給沈寧一張紙條。沈寧回到家里,才打開來,卻原來是一小塊草紙,上面用火柴頭寫著四個字:“不白之冤”。最近,沈寧又偶然找出了這張紙條,有朋友看到后,拿去復制了。 捐獻 沈寧因為要搬家,所以許多東西已經收拾起來,還有一些東西散在屋里,是因為這些是夏衍的舊物,準備捐獻的。有夏衍用過幾十年的一個半導體,從四十年代就開始用的幾個南方的老式的羊皮箱,幾個老式的書柜,也包括這雙皮鞋在內。沈寧覺得,紀念夏衍的地方,如果擺上這些舊東西,也算有個比較真實的氣氛。 對夏衍的遺物,沈寧雖然覺得有些不舍,但也想到這些東西留在自己這里,終不是長久之計,“我和孩子還覺得這些東西有意義,可是再下一代就不會再看重這些了,所以不如給它們找個好的歸宿”。今年上半年,北京的現代文學館動手最快,拿走了一批夏衍的藏書,還有夏衍用過的一張床、一把藤椅、一張茶幾和一個書架。中國電影資料館也要走了一大批書。夏衍收藏的郵票和書畫,主要捐給了上海博物館和浙江省博物館,這在他生前大多都辦完了。1989年10月,夏衍向上海博物館捐贈了納蘭性德詩翰手卷,他向浙江省博物館捐獻珍貴書畫101件,其中“揚州八家”二十五幅,絕大部分都是稀世珍品,另外還包括三十幅齊白石作品,和吳昌碩、黃賓虹、沈鈞儒、郭沫若的字畫。1991年,夏衍又向上海捐贈一批郵票,其中有一套紅、黃、綠色的三枚清代“大龍票”,是中國1878年發行的第一套郵票,價值連城。 夏衍的故鄉杭州方面也希望要一些夏衍的舊物。我10月12日最近一次到沈宅,聽說杭州已經來人把東西拉走了。在這些事情上,沈寧還是覺得上海人做事快。就在國慶節前,上海左聯紀念館的張小紅聽說了消息,專門跑來一趟北京,拉走了一批東西。 沈寧說,因為夏衍人緣好,所以他雖然不在了,可是大家都還很懷念他。 夏衍的“新書” 夏衍的著作“文革”后出版了很多,其中以《懶尋舊夢錄》(三聯版)最為著名,此書最近已由三聯重印。成規模的結集一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擴充、再版《夏衍選集》和四川文藝出版社1988年7月出版的四卷本《夏衍選集》(此書九十年代曾再版),二是由會林、紹武編、中國戲劇出版社1984年10月出版的《夏衍劇作集》,三是中國電影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夏衍電影劇作集》。夏衍的傳記,1985年6月,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了會林、紹武著《夏衍傳》,1994年12月,上海文藝出版社還出版了一本周斌著的較簡略的《夏衍傳略》。 今年是夏衍一百周年誕辰,還有夏公的著作即將出版,中國電影家協會編輯了《論夏衍》,中國電影資料館編輯了《夏衍電影論文集》等。 今年7月,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了《夏衍散文》,收有夏衍晚年的文章若干,是該社“世紀文存”之一種。同時,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了夏衍的《包身工》和《上海屋檐下》,作為“百年百種優秀中國文學圖書”的兩種。新書剛剛運來一批,在書架上安靜地或站或臥,望著這所老房子。不久,沈寧就要搬出這里了,這批新書也會和它們的主人一起告別這個院落,找一個新家。 摘自《中華讀書報》2000.10.25
|
|
.本網站所刊載信息,不代表中新社觀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