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mlr8.com | 2000年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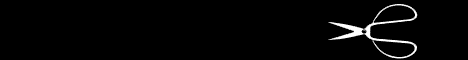 |
阿劍
我出生在中國的廣西壯族自治區一個叫全州的小縣,聽父親說那兒與湖南接界,先前常發生邊界沖突。父親就是在械斗中打死了人才偷渡到越南境內的。我的母親是個很漂亮的女人。別人叫她「小白菜」。我們父子逃跑后她一度瘋了,聽說后來同一個姓丁的屠夫結了婚,生了個小妹妹,現在上到中學了,據說長相與我很像。不過她應該比我幸福得多,有時候我非常迫切地想看看她和媽媽。 我們從越南輾轉到泰國吃了不少苦頭,「蛇頭」引誘我們說這邊很容易發財,事實上只是為了收取我們一大筆偷渡費,為此,父親還賣掉了他的一個腎。同我們一起偷渡的有十多個越南人,還有幾個中國人,后來其中的一個小男孩也做了「人妖」,我在曼爾鎮演出時還碰到過他。 我作「人妖」純粹是生活所迫,在泰國,只有窮人的孩子才會去干這個。我到泰國時已經6歲了,按理說早錯過了訓練的最佳時機,別人一般兩三歲就開始接受女性化訓練,但父親找不到別的希望,只好求人家收下我。由于我天生就比較女孩子氣,所以位于曼谷附近的那所專門培養「人妖」的學校收下了我,還給我取名叫尼莎,在當地話中是「乖妮」的意思(我的中國名字叫方××,現在父親仍習慣這樣叫我)。 最初人家騙我說是打預防針,我就很順從地接受了,后來我才知道注射的是女性激素。每天除注射激素外,還要進行形體訓練和舞蹈訓練,以適應將來的演出需要。窮人的孩子只有走這條路才可以相對多賺點錢,要不就得去做童妓,供那些戀態的人狎玩。 我到13歲那年就發育得非常好了,皮膚細膩,雙乳高聳,臀部渾圓,說話也非常女性化了。除了指關節比一般女性略粗外,別的根本看不出是一個男子身。 我14歲時開始參加芭堤雅的「蒂卡薩」歌舞團演出。芭堤雅人口不足5萬但每年接待350多萬游客,是泰國最著名的「人妖」娛樂城。 我所在的歌舞團規模算小的,才十多個人,但每月收入仍上億泰銖。由于我來自中國,會講漢語,所以團里很看重我,讓我兼任報幕員,用英、中、日三種語言進行內容介紹。我父親現在團里打雜,月薪850泰銖(折合人民幣280余元),我的收入自然高些,有6000多泰銖,但我還要購買藥品和化妝品以維持美貌,而在泰國,這些東西出奇地貴,事實上我每個月的純收入也是非常少的。 更讓人不敢想象的是,干我們這行吃的是「青春飯」和「色相飯」,到30多歲「人老珠黃」,團里就會叫你開路,而除了唱歌跳舞之外,我們什么都干不來,先前的收入只能用來糊口,自然買不起維持美艷的昂貴藥品,而一停藥,身體就會變形,變得奇形怪狀。有的人因不堪其丑而選擇了自殺。而事實上,大部份「人妖」一般也就活個40多歲,生命便宣告終結了。 我們歌舞團的老板叫巴猜,他知道我們這個歌舞團在小城排不上號,為了吸引觀眾必須別出新招,所以他常常想些新點子,例如讓觀眾給我們拍裸照,與我們單獨接觸,這些大膽舉措都是我們團先搞起來的,要不是他的這種「開放意識」,你們也不可能采訪到我,別的團都有鐵規矩,不準接受觀眾的私人邀請,更不準披露個人的情況。 來看表演的有很多是中國人,聽說前些年你們那兒政府管得很死的,其實,相對來說,「人妖」表演算是比較高雅比較正規的,色情的成分不多,也不嚴重。再說,實際上觀看者和表演者大都是一樣的男人嘛,泰國的法律也承認我們的男人身份。 我們每晚演兩場。一般表演熱情奔放的泰國土風舞和現代迪斯科,這些容易煽動觀眾的情緒。當然我們也表演典雅的法國宮廷舞和中國古代霓裳舞,別忘了,我們自小都受過良好的形體訓練和舞蹈訓練,屬于很專業的演出。再說,我們的布景、服裝、燈光、音響都是一流的,我們并不是簡單的以變性和色相來吸引觀眾的。因此每場480泰銖的價位觀眾都樂意接受,幾乎場場爆滿,每場可為老板賺上幾十萬泰銖。 別看我們在舞臺上飄然若仙、笑容可掬,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辛酸事:這一輩子結婚是不可能的了,即便過正常人的生活都只能是我們的一個夢想。你注意到剛才演出時我身邊那位束高髻的「靚妹」了嗎?別看他演出時激情四溢,其實他曾兩次自殺過。他平日喜歡讀點書,比我們有文化,時常為自己這種不尷不尬的身份痛苦。他家里也最窮,全家四兄妹、三個男孩子有兩個做「人妖」,最小的妹妹在一個色情歌舞團賣笑。他和我比較要好,他一直勸我盡快與中國的親人取得聯系,申請回到中國。一次被我爸聽見,發了脾氣。老爸一直不肯接受媽媽再嫁的事實,再說他還犯有命案,家里人都以為我們早野死在外面了。還有,我現在的「人妖」身份,在中國肯定讓人接受不了。 我希望有一天能回美麗的祖國看看,我6歲離開中國,至今已有15年了。15年來,我常常在夢中回到童年玩耍的那片沙灘、草地。父親說過帶我去桂林,那兒是聞名天下的風景勝地,可惜3個月后他就出事了,因此我至今都沒見過漓江和象山,只能從畫片上去感受桂林山水。泰國這兒出版過一本《中國的名勝古跡》,我一見毫不猶豫地買了下來。 父親也非常想回國,你別看他發火時說決不回去,其實他常常念叨我母親的小名。有時我半夜里醒過來,見他一個人孤零零地對月落淚,我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可憐的父親,他到泰國后清過垃圾、挖過墓坑,還差點被人拉去當「托」。他身上少了一個腎,出不得苦力,只好撿些輕巧的下賤活干。剛來時,我們講不來本地話,還常被人欺侮。 在離我們這兒大約300公里的地方有一個叫卡里尼的小鎮上住著一個老人,是我爸在泰國唯一認識的華人,每年的春節,他們總要聚在一起按中國的傳統過節,而我是走不開的,老板很少給我們放假,他必須趁我們年輕貌美時從我們身上盡可能多地榨取每一點利潤。當然,我們自己也必須爭取時間掙養老金,否則等30來歲被拋棄時,生活就沒有著落。 (摘自《特區青年報》99.9.24) |
最近更新日期:2000年02月18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