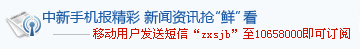殘酷社會樂觀而活 聽“真實”蔡康永的自我解讀

(聲明:此文版權屬《國際先驅導報》,任何媒體若需轉載,務必經該報許可。)
蔡康永,生于1962,臺灣節目主持人、作家。1990年獲得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電影電視研究所編導制作碩士學位后,返回臺灣參加電影制片以及編劇、影評的工作。主持過名人訪談《真情指數》等節目,綜藝節目《康熙來了》最為成功。連續4屆主持金馬獎頒獎典禮。曾任時尚雜志《GQ》臺灣版創刊總編輯并登上封面,出版多本散文著作,包括《痛快日記》、《LA流浪記》和《那些男孩教我的事》等。
【先鋒語錄】
★你一定是先知道最殘酷的事,才會樂觀得起來。
★娛樂圈的人堪稱是在傷害中茁壯的人,因為爛新聞勝過沒有新聞。
★我稱韓寒是俠客,那是因為他就是俠客,而我不是啊。
“看康熙的日子很無聊,不看的時候更無聊”,很顯然,大陸網友喜歡《康熙來了》是有理由的。
節目里的小S永遠很豪放、蔡康永永遠很酷、很淡定,矜持得就像站在他肩頭的那只烏鴉。若不是真的坐在他面前,聽他一字一句和你玩語言的捉迷藏,你不會認識真實的蔡康永,但是,聊了一個半小時,對于哪一個才是真實的蔡康永,你極有可能更不確定。
我是一個很勇于認錯和改變的人
蔡康永最厲害之處,在于他總是能獨一無二地思考。
想不到他也偶有凌厲的表露,“江湖行走,難免出劍傷人”,《康熙來了》的刀光劍影里來去,他像個超脫疏離的第三者,早已冷眼看透娛樂圈的傷害與復仇,所以膽敢揭短、也膽敢拍一部關于娛樂圈真相的電影;而對于某些脈脈的溫情,他同樣無法抗拒,一如面對小S他總忍不住要歡喜。某次秀場,有曾在巴黎艱難求學的模特過來擁抱,是《康熙來了》令她熬過異國歲月,康永說:“我很高興自己留下了一些痕跡。”
學電影的他,卻是以娛樂主持的角色“留下些痕跡”,至于何時退出娛樂主持,他說主要取決于小S,“如果她也覺得,好啦,就這樣子吧,那么就沒了,如果‘康熙’沒了,那我就沒有理由主持別的東西了。S現在還蠻戰戰兢兢的,因為她知道一懷孕的話,責任就在她身上。”他忍不住笑著說。
《國際先驅導報》:蔡康永身上有很多天生的東西,很多問題只有你才會用這種思維去想?
蔡康永:好像是,我不太明白為什么,也很驚訝為什么別人不這樣想。可必須要說我是一個很勇于認錯和改變的人,我到現在都還是在節目中聽到某一句話,回到后臺就會想:哦,原來可以這樣子,然后就改了。我善于把舊的東西去掉,比如我的微博一直在刪掉,別人就說為什么要刪掉?我就會說為什么不刪?書店里面這么多書,有些放在書架上也可能一輩子都不會有人拿下來看,很多作家對我來講就是已經不見的人,他出了書,根本就沒有人買,放在架子上一輩子,那個就叫做不見,所以在我看來,如果你的微博超過了一千條,一百條之前的一百條那都是不見的,人家對你興趣的容量可能就是六十條,那你就要一直推陳出新,讓人家看到新東西。
就像《康熙來了》一樣,S和我很少回顧說哪一集怎么樣,有很多經典的畫面我自己都覺得很好笑,不知道自己在干嗎,做出一些神經病的事,場面不可收拾,但也就過去了。在臺灣,我們已經很習慣快速遺忘,再怎么瘋狂的、引起議論的事都會一下就過去了。所以我現在碰到厲害的人,我還是很喜歡聽他們講話,因為他們永遠都會給我一個想法,就是原來可以這樣看事情。
Q:所謂厲害的人,是哪一些?
A:各式各樣,以前做一對一專訪的時候,我開訪問對象的名單,制作人都會昏倒。一個數學家得了國際天才獎,我要訪問,或者一個教宗,我也想訪問。我很想知道數學家腦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很想知道教宗那么老了,接近死亡,他是不是覺得上帝一定會給他一個好的待遇?其實根本是我們的行業誤會了世界上的人想事情的方法,娛樂圈的人都很幼稚,整天都在玩,講講笑話、唱唱歌、跳跳舞,逗人家開心就覺得好棒,以為全世界都長得像玫瑰花園,可殊不知你只要跨出去一步,政治圈、企業圈、宗教界,每一個地方都殺人,都血流成河,哪有你想得那般輕易。
有一次,我訪問圣嚴法師,他說,在紐約時,曾被人帶去練氣功,去之前很多人說這個師傅很厲害,因為照他的方法運氣,就會跳出一種從未見過的舞蹈,圣嚴法師就去了,果然二三十分鐘后,他手舞足蹈到停不下來的地步,最后倒在地上。當時我就說:“哇,那你一定覺得你原來的宗教信仰,抵不過這個老師吧。”圣嚴法師說:“沒有啊,我手舞足蹈了,就是這樣啊,這跟智慧一點關系都沒有,我從此知道有這一派,可是和我無關。”一般人手舞足蹈完了后,可能就說我跟著他走好了,可是圣嚴法師,就只是覺得這很美觀啊,依然回來信佛教,所以你就知道有各種想事情的方法。
Q:那你怎么去跟數學家對話?
A:像數學家我就會直接和他講,你這次得獎的這個超弦理論不要在節目里解釋給我聽,我也聽不明白,我的觀眾也聽不明白。我要問他作為一個天才數學家的孤寂和榮耀是什么,我的理論總是在想很根本的事情吧,就是他終究是一個人,多過他是一個數學家,或者是多過他是一個宗教領袖,那個是你要問的東西。
Q:你也不會問他是怎樣成功的?
A:我根本不太會認為他們會接受我們一般人對成功的定義。我和蔡國強很要好,有一次他被選入“一百位藝術圈有影響力的人”,我就說:“哇,你入選了。”他說:“對啊,明年就不會了。”每年都有一百個嘛,你今年進來明年出去。他說你不能那樣想事情,像諾貝爾文學獎、威尼斯雙年展,你一旦認為得了就成功了,你就中計了,那個都是別人搞鬼,然后把你頂出來配合演出,如果你以為自己是主角,那就搞錯了,諾貝爾文學獎的主角當然是諾貝爾文學獎啊,得獎者每年換一個嘛,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啊。
我的電影一定會傷害到人
蔡康永曾說,等到他厭倦了五光十色的熱鬧的時候,還給自己留了一個好玩的東西——比方說寫東西,或拍一部自娛娛人并且不太浪費別人錢的電影。現在,他還沒有厭倦娛樂圈的熱鬧,就開始拍電影了。并且兩部同時進行,“一個很頑皮、有點粗野,另一部很漂亮”,聽來就好像一個立志要生兩個孩子的媽。
Q:你也是娛樂圈里的人,做揭露娛樂圈的電影怕不怕構成傷害?
A:應該會吧,就像《康熙來了》不斷地在傷害我們圈子里的人一樣,《康熙來了》是眾矢之的,就是沒有辦法,我們不管做什么事情,一方面在被重視的同時,也就會構成某一程度的傷害。娛樂圈的人堪稱是在傷害中茁壯的人,因為爛新聞勝過沒有新聞,就是你不上報才會想死,就是上了報是爛新聞都勝過不上報,所以娛樂圈的人的確精神狀態比較能接受就是一邊挨刀子一邊噴著血,然后形成美麗的花朵,所以你講的這個事情,《康熙來了》每天都在演練,所以我的電影一定會傷害到人,這已經是我們習慣的模式了。
Q:你以前做過根據白先勇先生小說改編的電影《最后的貴族》的編劇,白先勇比較喜歡寫離亂中的愛情和人的命運,來反映一些深沉的家國情懷,你會不會也拍更深沉一些的電影?
A:我就算拍深沉的東西,恐怕也不是家國情懷,因為我的童年都泡在這個氣氛里,對我來講這已經很夠了,如果長大之后又再拿出來回味,對我來講好煩啊。所以我一直都這樣,像張愛玲的《小團圓》我到現在都沒有讀,再好的作家我讀到他的四本或五本書就夠了。我對舊上海、對往日情懷的感覺,就是一旦覺得夠了,那就夠了,人生還有很多好玩的事情,不能一直在這里面攪和。
我覺得我可能會拍吸血鬼吧,那是我的深沉,我會想說沒有死亡那是什么樣的感覺啊,如果有一個吸血鬼很想要試試看死掉是什么滋味,然后就一輩子都在自殺,會不會有一個很深沉的東西出來,就是人家都想活久一點,但是他就想死掉。我小時候看京劇看昆曲,那些東西在我生命中占的比重已經夠了。
韓寒是俠客,我是散人
蔡康永很早就說,人生本來就是矛盾體,他自身也是,一方面趨利避害的實用主義原則若燈塔般指引著他的為人做事,另一方面叛逆、大膽,成為傳統文化浸淫出來的最閃亮“逆子”。
他是最早“出柜”的臺灣娛樂名人,他的言行總是辛辣大膽,但他卻是出身教養十足的富裕貴族,傳統修養深厚,6歲便登臺唱京劇《四郎探母》,至今仍能背出大段的《論語》,他心中的孔子絕對是一個充滿生命力、熱情洋溢的人,因為他覺得真正叛逆的人都非常重視傳統,只有當你把傳統當成是一個夠分量的力量,你才會奮力跟它搏斗,你才會把它當作是一個足以尊敬的對手,然后從傳統當中產生出新的創作生命來。
他曾主持一檔名人訪談節目《真情指數》,但有著強烈生命力的妓女、愛唱歌的小孩子的邊緣人生對他的吸引力更大,因為他篤信:成功不應該被界定為人生唯一的價值,他從來不覺得自己成功,“人生一定要成功嗎?失敗的人難道不值得有一個好的人生嗎?”
2005年,他對大學生們說人生的意義就是能否耐得住不被關注的寂寞,留下點東西,讓世界變得不一樣,讓世界變得更值得活。而現在的他,只想做個無拘無束、閑散自在的散人。
Q:你在歷史的熏陶中長大,那你最喜歡哪個時代?
A:我覺得我在魏晉南北朝會活得很好,因為我就是一個講空話的人,講了兩三句漂亮話,人家覺得你還挺有趣的,可是什么事都做不成,就像《世說新語》里面的那些貴族,搞得民不聊生、亂七八糟。
但如果真的問我,我其實比較想要十年后。有了網絡以后,事情的變化很快,不像清朝的十年前和十年后沒有什么差別,現在的十年后很令人期待。十年后不知道跑出多少個像微博一樣的新鮮東西來,有一天如果大家的腦波可以用紅外線連起來,想事情可以不用傳短訊就傳過去,那都很好玩,所以我不信電影里面拍過去的時代,過去的巴黎整個街道都臭死了,尿味和馬車的糞便,動不動在巷子里被壞人抓去打一頓,就把錢搶走了,那到底有什么好向往的,你還以為那里多優雅?
Q:你對于存在感是怎么理解的?你剛剛說想去十年后,那如果說十年后蔡康永被人遺忘呢?
A:其實存在感,即使通過和一個人談戀愛也能夠得到。我們常常覺得明星的生活不會失去平衡,是因為他需求無限大的存在感,他有了五萬個粉絲,他要五十萬,可是人的感覺大概到了一個程度,就麻痹了。所以我常常講湯姆·克魯斯、妮可·基德曼,在好萊塢的時候看到賬面上中國票房收入一億,會覺得很好,可是你說現實生活中他們有辦法想像河北省那五千萬個粉絲在想他們嗎?就像周杰倫開八萬人演唱會的時候,他感覺得到八萬人對他的存在感,可是等他的唱片賣到非洲去,那個就已經超過他能感受到的能力了,所以明星的不會失去平衡是建立在他知道停在哪里,這樣就夠了。
《康熙來了》是一樣的狀況,S和我完全沒有希望過無限大,我們完全可以接受好萊塢的人就完全把你當路人一樣。所以我們到一個程度,S就去結婚生小孩,她會感覺到她的存在感真正是來源于女兒和丈夫對她的認定,那就夠了。你身邊的人鞏固了你的存在感,我覺得那就是至上的幸福。如果有八萬人為你尖叫,可是你回到家沒有人在乎你,你仍然不會感覺到存在感。
Q:你現在已經接近“知天命”的年紀了,還有困惑或者期待嗎?
A:有啊,我有很多困惑,我覺得那是活下去的動力,我覺得知天命是一個很可怕的境界,我不信這個,古人這么說,因為中國古人活得比較短的關系,他們可能覺得活到五十歲,就宇宙都知道了。人到了一定年齡,會比較沒有尖銳的雄心,所以我稱韓寒是俠客,那是因為他就是俠客,而我不是啊。
Q:那你是什么?
A:我是散人吧。太散了,我覺得俠客比較有實力感。我就覺得如果我做了一件把我自己陷入泥沼的事,我會很恨我自己啊,如果你要讓我拍《赤壁》,我就會一邊拍一邊問自己為何不拍一個輕松一點的。(賈悅琳對本文亦有貢獻)
社會并非充滿善意
《國際先驅導報》文章 兒時的優良教育,使蔡康永懂得許多做人的圓通,例如不太會對別人的事情指手畫腳,最出格也就是在微博上自說自話半遮半掩地“給殘酷社會的善意短信”。事業上他并無太大野心,在臺灣養尊處優慣了,便比較懼怕來大陸發展。對于大陸,他始終是這樣,保持著一種座上賓客的禮貌與距離——他會通過微博和博客來關注大陸,會用同樣的熱情來回應大陸的熱情,但是,這熱情表現得委婉而小心翼翼,“我都會關注,可是不能發言,因為客人就是客人,”——在他看來,這也是有教養的表現。
Q:你會不會關注大陸的現實問題,比如房價高漲,社會的浮躁?
A:我都會關注,可是不能發言,因為客人就是客人,不能講別人家里的事,我懂那個心情,比方說現在如果有人蓋了一個豆腐渣的校舍,就是當地人可以講的,可是香港或者臺灣人關心這件事,有的人會難受,因為不知道你的出發點是嘲笑還是關心,所以有教養的小孩就會很尊重這種事情,就是到人家家里看到壁紙剝落了,你不用講說:啊,壁紙掉下來了。這不關你的事。
Q:你在微博上寫了《給殘酷社會的善意短信》,殘酷社會如何樂觀而活?
A:你一開始如果就知道這是殘酷社會,我覺得會好很多。我一開始為什么會定這個標題,就是因為你不能很天真地認為這是一個充滿善意的社會,娛樂圈的殘酷和整個社會的殘酷是同一種,就是你很難出人頭地。這一點你真的不能去騙別人,你不能像老師在學校里騙學生那樣說假如你努力就會成功,假如你很勤勞就會賺很多錢。沒有,社會不是用這個方式來回報你的,所以你一開始就認定了這些都不會發生,你就會有心理準備,你就不至于會認為人生那么難度過。所以我說“人生終有一死”,它很殘酷,可又是人生最簡單的真理,你知道這件事,你就會立刻醒過來說:哇,我只剩兩萬天可以活了,趕快去做你想做的事。我覺得你一定是先知道最殘酷的事,才會樂觀得起來。記者陳雪蓮、楊梅菊發自北京
 參與互動(0) 參與互動(0) |
【編輯:李季】 |
Copyright ©1999-2025 chinanews.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