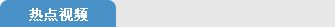- "專職釘子戶"反對強拆 稱對曾經的過失行為贖罪

從12月7日被朝陽一家餐廳聘用,陸大任天天在店里為別人做著“釘子戶”,在忍受著斷水斷電生活的同時,他則把這視為一種贖罪。很少有人知道,陸大任曾做過四年的拆遷隊長。當年,一名自殺的釘子戶讓他良心備受譴責,他曾發誓一輩子不再干拆遷這行。
調研科長下海入行房地產
陸大任,體形微胖,濃眉,杏眼,戴著一副銀邊眼鏡,頭發花白,梳著發髻。他說起話來,聲音渾厚有力,身邊的朋友都說他長得像小品演員范偉。
做釘子戶的這些日子,整日寂寞難耐,反倒讓他回憶起不少當年拆遷的事兒。
“我28歲就在山西一事業單位的調研科做小官了,當時主要做一些市場調查,信息匯總或者一些商業信息。”陸大任笑著說。
后來,生活出現了轉機,在事業單位的第6年,陸大任的一位叔叔從香港回晉投資房地產,他進入房地產公司幫忙打理瑣事,就這樣下海了。
“當然,之前單位的工資也按時領取,雖然只有200多元,但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還算可以了。”陸大任說他在房地產公司只是做些小事情,掙錢也不多,四五年過后,公司一個運輸隊就交給他打理了,這是個油水很大的行業,1年下來能賺60萬。
拆遷隊長目睹自殺釘子戶
熟悉了房地產公司,陸大任開始涉足房屋拆遷。
拆遷的日子,被陸大任稱做“永遠抹不去的心痛”。
他說,做拆遷隊長有四年時間,收益過百萬。按照他的說法,那時候錢好掙,做拆遷也不難,很少有現在所說的釘子戶。遇上個別不想拆遷的房主,直接拿著禮品和現金跟他們談判,一般也就同意了。
隨著時間推移,也慢慢出現了釘子戶,拆遷難度增大了,但這并沒有難倒曾經做爆破兵的陸大任。
“我們也開始強拆了。”陸大任說,1998年在邯鄲的一次拆遷中,他遇到了3家釘子戶,拆遷隊就在房子不遠處放炸藥,這樣本來就有裂紋的房子變得搖搖欲墜,房價也隨之貶值,拆遷隊繼而得以能順利拆遷。
一開始,他們強拆時有所顧慮,躲在房子不遠處看著,不敢靠前,怕房主報復;后來麻木了,強拆的時候陸大任就坐在附近酒館喝酒。
酒后的陸大任常常感到心靈不安,覺得自己干強拆是傷天害理的事兒。
2001年,也是在邯鄲,在給付釘子戶30余萬元拆遷補償款后,陸大任帶領拆遷隊,用推土機推平了房屋。一個男主人不知道補償款已到位,一頭撞死在推土機上。
此后,陸大任離開拆遷隊。出于良心譴責,他曾發誓一輩子不再干拆遷這行。
“專職釘子戶”遇兩撥黑衣人
2009年12月7日以來,陸大任看到招聘信息成了“專職釘子戶”,這種身份的轉變,距他做拆遷隊長整10年。
位于安定路鳥巢旁的魚堡餐廳,因陸大任這個專職釘子戶而被眾人關注。
12月18日,北京很冷,氣溫低至零下10攝氏度。陸大任一如既往的打扮:棉帽,軍大衣,棉褲,靴子,守在飯館內聽廣播,屋內沒水沒電,廣播是他唯一的伴兒。
中午,陸大任吃的盒飯,身旁一個廢棄紙箱里裝滿了塑料飯盒,門口放了兩袋饅頭,有十多個,“屋子冷,一會就餓,餓了就用煤爐烤個饅頭吃”,陸大任說。
由于停水停電無暖氣,他只能去附近居民家借水,并用爐子燒蜂窩煤取暖。
“就這還得偷著燒。”陸大任剛說完,飯館進來4個人,“不是告訴過你不能在屋里用煤爐嗎?快拿出去,給他開條!”他們說。
他們是綜合治理辦公室的人,陸大任立刻把煤爐拎了出去,“我明白,他們是為了我好,怕中煤氣出人命。”
為了守住飯館的一畝三分地,陸大任絞盡腦汁。他用石塊在餐館門口圈出界限,提醒對方2米之內請勿靠近,同時他還在餐館門上貼出大字報,標明已被停水停電幾天,提醒拆遷方注意自己的行為給商戶造成的損失。
陸大任“上任”半個月來,遭遇過兩撥“黑衣人”。
一次是在10天前的一個凌晨,迷迷糊糊醒來,看見幾個“黑衣”試圖拆除餐館門口的地磚,被他發現勸阻了。
昨日,數十“黑衣人”再次光顧,這次沒那么幸運,陸大任被6個人強行抬出餐館。
陸大任說,釘子戶與對方玩的就是心理戰。只要意志堅韌死守,一定能拿到補償。
陸大任
男,46歲,山西太原人。
曾在山西某事業單位任職,后下海經商。現在北京做“專職釘子戶”。
本報記者 劉澤寧 實習生 劉一鵬
我國實施高溫補貼政策已有年頭了,但是多地標準已數年未漲,高溫津貼落實遭遇尷尬。
Copyright ©1999-2024 chinanews.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