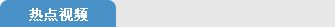- 國(guó)防科大教授將錢學(xué)森寫給他的部分信件捐給學(xué)校


10月31日,兩彈一星元?jiǎng)住⒅袊?guó)航天之父錢學(xué)森逝世,舉國(guó)哀悼。在國(guó)防科技大學(xué)校園里,一名老教授聞?dòng)嵰彩潜床灰选?/p>
“錢老去世的消息傳來后,這些天,我一直沉浸在悲痛之中……”昨日,在國(guó)防科技大學(xué)舉行的錢學(xué)森親筆書信捐贈(zèng)儀式上,該校譚暑生教授將錢學(xué)森寫給自己的部分信件捐給了學(xué)校,隨后,他深情地回憶起自己與錢學(xué)森20余年的交往經(jīng)歷……
“你們學(xué)校真有人才!”
——因一篇論文與錢老結(jié)緣
譚暑生與錢學(xué)森的交往,緣于他發(fā)表于國(guó)防科技大學(xué)學(xué)報(bào)上的一篇論文。
從小學(xué)到大學(xué)畢業(yè),譚暑生的學(xué)業(yè)成績(jī)始終出類拔萃。讀大學(xué)時(shí),他選擇了物理學(xué)專業(yè),希望發(fā)現(xiàn)以中國(guó)人名字命名的物理學(xué)理論、方程或定律。大學(xué)畢業(yè)后,他先后在上海等地從事技術(shù)工作,加深了對(duì)物理學(xué)的理解,訓(xùn)練了相應(yīng)的動(dòng)手能力。后來他調(diào)入國(guó)防科技大學(xué),從事激光技術(shù)研究和物理教學(xué)工作。
譚暑生的辛勤付出終于有了收獲。1983年底,他的一篇關(guān)于“標(biāo)準(zhǔn)時(shí)空論”的論文發(fā)表于國(guó)防科技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博得了學(xué)術(shù)界的一致好評(píng)。沒過多久,國(guó)防科大趙伊君教授專門將譚暑生的這篇論文送給錢學(xué)森指導(dǎo),錢學(xué)森仔細(xì)看過這篇文章后,充分肯定了譚暑生所取得的學(xué)術(shù)成果,他對(duì)趙伊君說:“你們學(xué)校真有人才!”
1984年2月16日,錢學(xué)森給趙伊君寫來了一封信。在信中,他闡明了自己對(duì)于“標(biāo)準(zhǔn)時(shí)空論”的看法,認(rèn)為“標(biāo)準(zhǔn)時(shí)空論”成立。同時(shí),他還建議譚暑生改寫一下論文,特別是“引言”,說明該理論是完整理論之一部分,有其適用的范圍,而在其適用范圍內(nèi),它又是很精確的。錢學(xué)森表示:“這個(gè)觀點(diǎn)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的,也是我們比外國(guó)人高明之處。”
錢學(xué)森的信給了譚暑生極大的鼓舞,他覺得自己離成功又近了一步。為了將全部精力投入到科學(xué)研究中,譚暑生主動(dòng)辭掉了所擔(dān)任的行政職務(wù)。
寫去的信
錢老基本上都要回復(fù)
隨后,譚暑生每當(dāng)在學(xué)術(shù)研究過程中有什么新的進(jìn)展,或者遇到什么困惑,他都會(huì)寫信給錢學(xué)森,而錢學(xué)森基本上也會(huì)每信必回。為了讓譚暑生能潛心于科學(xué)研究工作,錢學(xué)森還多次給國(guó)防科大領(lǐng)導(dǎo)寫信,說“譚暑生的研究室做理論工作,大概花不了什么錢,應(yīng)該下決心干。”
1985年12月31日,錢學(xué)森在給譚暑生的信中寫道:“今天已是1985年的最后一天了,所以我首先要向您拜年!全中國(guó)搞理論工作的同志的日子都難過,但中國(guó)的事總是一步一步向前發(fā)展的,明年一定會(huì)比今年好!在前幾天文化部舉行的社會(huì)主義文化發(fā)展戰(zhàn)略討論會(huì)上,我說一切科學(xué)理論研究的價(jià)值不在于短期的實(shí)用,而在于文化建設(shè)。科學(xué)理論是社會(huì)主義文化!沒有科學(xué)理論就談不上21世紀(jì)的社會(huì)主義文明。讓我們大家來宣傳這一真理,我們不講誰講?請(qǐng)相信日子會(huì)好起來!”
就這樣,在錢學(xué)森的鼓舞下,譚暑生多年來一直矢志于理論研究工作,并且不斷取得新的突破。后來錢學(xué)森的身體狀況沒以前好了,他才停止給譚暑生親筆回信。譚暑生已習(xí)慣了給錢學(xué)森寫信匯報(bào)科學(xué)研究的新進(jìn)展。收到譚暑生的信后,錢學(xué)森仍會(huì)安排秘書打電話回復(fù)他,對(duì)他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表示祝賀。
錢學(xué)森在1996年5月19日寫給譚暑生的最后一封親筆信中說:“對(duì)您近年來的不斷探索精神,我要表示敬意!但我非此道行家,不能再說更多的話……”
2008年6月,凝聚了譚暑生多年心血的研究成果《從狹義相對(duì)論到標(biāo)準(zhǔn)時(shí)空論》正式出版。在該書的前言部分,譚暑生表達(dá)了對(duì)錢學(xué)森的敬意與感謝,說“他的關(guān)懷和支持是我能夠20余年磨一劍的最重要的外部支撐條件”。隨后,他及時(shí)將書寄給了錢學(xué)森。沒多久,錢學(xué)森要秘書給他打來電話:“錢老收到您的書后非常高興,希望您不斷創(chuàng)新,勇于挑戰(zhàn)權(quán)威,為中國(guó)科學(xué)家爭(zhēng)光”。
謙虛的錢老
將褒揚(yáng)自己的文字畫了個(gè)“×”
譚暑生說,錢學(xué)森不僅是聞名國(guó)內(nèi)外的大師級(jí)科學(xué)家,又身居重要的領(lǐng)導(dǎo)崗位,卻非常謙遜,沒有一丁點(diǎn)架子,給他的信中總是尊稱“您”,并多次表示要“相互學(xué)習(xí)”。1984年8月,重慶大學(xué)學(xué)者孫起村給錢學(xué)森寫了一封信,向其請(qǐng)教物理理論方面的問題。錢學(xué)森將這封信轉(zhuǎn)給了譚暑生,請(qǐng)他代為回信給孫起村。譚暑生注意到,錢學(xué)森將孫起村信中有關(guān)褒揚(yáng)自己的話畫了一個(gè)大大的“×”字。
錢學(xué)森嚴(yán)謹(jǐn)認(rèn)真的態(tài)度,也深深地感染著譚暑生。1983年,錢學(xué)森給譚暑生寄來了一篇發(fā)表于外文版《科學(xué)文摘》上的理論文章,供他參考。由于擔(dān)心譚暑生與其他文章混淆,錢學(xué)森將這篇文章用彩筆做了標(biāo)記,并在其他無關(guān)文章上畫“×”。還有一次,錢學(xué)森在國(guó)防科工委資料室發(fā)現(xiàn)了一本名為《整體論和隱秩序》的外文書籍,他覺得對(duì)譚暑生的研究有幫助,遂將該書寄給了譚暑生,但不忘叮囑他“請(qǐng)您復(fù)印一套,用完后務(wù)必寄回給我,以便及時(shí)歸還。”
三次拜訪
感受大師的平易近人
為了當(dāng)面向錢學(xué)森請(qǐng)教,譚暑生曾先后三次在北京拜訪了他。
第一次是在1986年6月的一天。拜訪前,譚暑生先通過電話與錢學(xué)森的秘書預(yù)約了時(shí)間。那天上午8時(shí)30分左右,譚暑生剛邁進(jìn)錢學(xué)森的辦公室,錢學(xué)森便從椅子上站了起來,如老朋友般緊緊握著他的手說:“您搞出了這么個(gè)理論,真是很不簡(jiǎn)單啊……”見錢學(xué)森如此平易近人,譚暑生剛開始時(shí)的緊張情緒蕩然無存,接下來無拘無束地和他暢談起來。期間,秘書多次進(jìn)屋,說還有人要向錢學(xué)森匯報(bào)工作,錢學(xué)森均讓他們下午再來。
不知不覺間,3個(gè)多小時(shí)過去了,譚暑生這才依依不舍地告別了錢學(xué)森。離開時(shí),譚暑生準(zhǔn)備將從湖南帶去的一幅湘繡送給錢學(xué)森,但錢學(xué)森怎么也不肯要,說自己從來不收別人的禮物。最后,譚暑生指著繡在湘繡上面的“松鶴延年”幾個(gè)字對(duì)錢學(xué)森說:“我是希望您健康長(zhǎng)壽啊,這幅湘繡表達(dá)了我和其他科技工作者對(duì)您的美好祝愿。”錢學(xué)森見譚暑生說得在理,才勉強(qiáng)收下。
此后的1987年和1988年,譚暑生又兩次在北京拜訪了錢學(xué)森,錢學(xué)森每次都要和他談三四個(gè)小時(shí),話語間滿是關(guān)切與鼓舞。錢學(xué)森還送了大量的書刊雜志給他,要他拿回家好好研究。
20多年間,雖然錢學(xué)森親筆給譚暑生寫來了30多封信,還先后三次見面,但譚暑生一直為自己未能與他合影而深感遺憾。
譚暑生表示,他準(zhǔn)備近日赴北京吊唁錢學(xué)森,送錢老最后一程。而錢老20多年間對(duì)他的關(guān)懷與教導(dǎo),錢老樸實(shí)無華的平民風(fēng)骨,將激勵(lì)著他今后在科學(xué)研究的道路上,義無返顧地走下去(陳國(guó)忠 王珺)
- ·不舍旅澳大熊貓回國(guó)!澳大利亞將租期延長(zhǎng)5年
- ·歷時(shí)3年跨越33國(guó) 荷蘭男子完成電動(dòng)車環(huán)球之旅
- ·佛羅里達(dá)州國(guó)家捕獲巨蟒 長(zhǎng)度超5米體內(nèi)有73顆蛋
- ·福原愛平安產(chǎn)下二胎 老公江宏杰喜曬一家四口(圖)
- ·加拿大一柴犬因會(huì)畫畫走紅 畫作已售出逾231幅
- ·加油槍未收司機(jī)駕車而去 加油站上演驚魂瞬間
- ·漂洋過海的“洋美猴王”:把京劇唱給世界聽
- ·膠東烈士陵園入口垃圾遍地、停車亂收費(fèi)?官方回應(yīng)
- ·結(jié)婚率降離婚率升 是獨(dú)立意識(shí)崛起還是房?jī)r(jià)太貴?
- ·網(wǎng)紅年薪百萬?市場(chǎng)調(diào)查:僅20%的頭部網(wǎng)紅在賺錢
我國(guó)實(shí)施高溫補(bǔ)貼政策已有年頭了,但是多地標(biāo)準(zhǔn)已數(shù)年未漲,高溫津貼落實(shí)遭遇尷尬。
Copyright ©1999-2025 chinanews.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