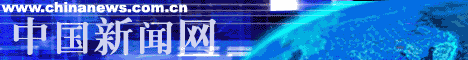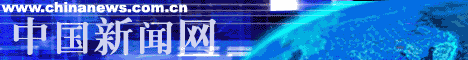陳道明準時出現在事先約好的地方。一副墨鏡,一身黑衣,清瘦。形象一如你熟悉的那般俊朗,甚至更年輕些。不過,陳道明真的47歲了,已經看不到當年《圍城》中方鴻漸那個油滑的影子。
風格因歲月而改變
說起《圍城》,陳道明倒有重新演一遍的想法。“現在讓我演圍城,可能會做一些改良,還會有一些不同。因為年齡不一樣,對人性、對生活的理解也不一樣。”
在《康熙王朝》中更多地使用眼神說話的陳道明,在評論自己的演技風格時,把歲月拉了進來。“我想,一個演員風格的改變,最主要的是因為歲月。一方面,經驗在不斷地積累,更重要的,就是理解也在逐步地深入。比如我自己,再過十年,對人可能又是更新的理解。演員不是一個玩世不恭的人,他不是為了表現而表現,而是因為理解而表現的。通過自己的理解去表現,然后再交給別人去理解。”沒錯。當年陳道明演完《圍城》時,沒人會想到2002年的陳道明是什么樣,沒人會想到他現在演繹的皇帝或者黑社會是如此的耳目一新。那么,十年以后的陳道明又會是什么樣呢?我對這個未知饒有興致。
攝影師一直忙著找拍攝的感覺:“你外衣太黑了,不好拍,脫了。”
陳道明很聽話地脫了外衣,里面還是一件灰黑的襯衫,于是打趣:“你不會還讓我脫吧?”一笑,很難得的詼諧:“這張臉沒法拍啊!哈。一張老臉。”
他寂寞地坐在我對面,我們四目相對,似乎無言。在我看來,陳道明的臉,依然是《末代皇帝》中那張年輕的臉。“所謂的平和,沉穩,也許是因為老了吧。這其中的關鍵,是我還算知道自己要什么東西。我知道要什么生活和哪些生活不是我的。這些一旦明確了,也就會平和了吧。”
“年輕人想改造世界,我從不反對。比如說,他們喜歡的東西,我也會去喜歡。我盡量以他們的意識形態去理解他們。因為我年輕時也受過年長者壓制我們、調理我們的痛苦。我幾乎不太對年輕人指手畫腳,我不干涉他們--包括對我的孩子。”
陳道明喜歡這樣組織語言:“他們年輕人……”或者“你們年輕人……”,但他絕不說“我們年輕人……”。
這一點,在他這個年齡層次的明星中,的確不多見。他很愿意正視自己的年齡,絕對沒有那種很勉強的老偶像做派。
“我覺得人應該真實些。我做這行31年,今年48了(虛歲--筆者注)。現在儼然一個很正統的老東西。做這行做了這么久,對這行的東西,不能說是看透了,也是看得多了,所以也就知道是什么樣了。年輕時候也虛偽、虛榮過,也幻想過,也為狹隘的目標追求過。以前覺得天下誰都不在,現在不,現在覺得天下誰都在。”
敬業之辨證理論
“我入行時沒有明星這個稱呼,統稱演員。充其量只有好演員、一般演員、不好的演員這些說法。我不喜歡明星,不知道算不算對新生事物的一種排斥。”
“我覺得,我是一個還能當演員的演員吧。的確有很多人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演員,卻在做演員,或者說自己根本不能做演員而不自知。在這點上,我對自己認識還算清楚。”
一直從事演藝事業的陳道明對敬業的問題有自己的看法。“敬業是么稀罕。可現在卻像好人好事一樣被表揚、被稱道,這不好。比如服務員賣東西,你就該賣得好,這應該說你做個售貨員還是稱職的,如此而已。可是一稱職就被表揚,這似乎不是很正常的事情。我覺得這是對比出來的。就是因為很多人賣得不好,或者根本不想賣好,總出差錯,于是比較出先進來了--這實在是不正常。你既然做這個,就應該稱職!否則就不要做!至于我,稱職而已。我只是做我該做的。”
我有時也浮躁
“浮躁?我覺得這是一個特別正常的社會人的心態。”陳道明聲音突然提高了,伸手指著自己,又指指我的座位說:“前兩天,也在這兒,我在這個位置上,劉震云在你現在那個位置上。我們倆為一個劇本聊天,屋里就我們倆。我們都覺得,現在很多中國人都缺少目的性。這一生啊,到底能干嘛,想干嘛,怎么干,其實并不是很明確。人人都在找機會,撞大運。我覺得,這不是特別踏實的社會心態、公民心態,這就是現在被稱為浮躁的東西。浮躁在哪兒?根源就是生活缺少目的性。”
“你的目的明確嗎?”
“非常明確:工作是為了休息,休息是為了工作。我覺得,人活得簡單一點才高級。對吧?”陳道明揚起下巴,是征詢共鳴的目光。
“你浮躁嗎?你的心靜嗎?”
“我?我也會有躁動不安的時候。人在對事物、對于自己沒有把握的時候就會煩躁。這也是很痛苦的,但這只是現象。剛才我說很多人生活缺少目的性,不知道做什么,所以就會煩躁。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應該順其自然,扭得太大會受傷的。”
拍完《康熙王朝》的陳道明迷上了康熙:“我欽佩他的智慧,他的忍痛能力。他承受著一般人無法承受的痛苦,而且具有非常人具備的智慧。”他有些沉浸地敘述著,如同追憶一個老朋友。陳道明曾經說過他對康熙有一種“男人式的崇拜”。這句話被很多人牢牢記住了。
戲里戲外,陳道明和康熙之間的神似,常常讓人迷惑。在別人眼里,陳道明超乎尋常地理智。
關于表達:不要讓我和你一樣
我聽說,陳道明輕易不接受采訪,還會在采訪中突然問記者一些問題,以達到反采訪的目的。幸好,我沒有遇上。但他常在關鍵問題上打斷我,迫使我不得不重新探尋他的內心。
“低調不代表沒調。我低調跟我的性格有很大關系。就是說,有些人愿意轟轟烈烈地生活;有些人喜歡離群索居的生活,少一點社會,給自己多一點。我是屬于后者,能在家里呆著,絕不出門。我所謂的低調,主要是我感覺很多時候說出來的話都是廢話,那還說他干嘛?不如閉嘴。”
“其實演員這個職業,是一個社會異類群體,也就是個別的群體。它的個別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我始終覺得媒體是這個‘部落人’的修正主義者。很好。”陳道明倚坐著,手指間夾著一支沒有燃盡的煙。
“我始終認為,中國人很優秀,沒什么太大的劣根性。但是,我也很悲哀地承認,國人與國人之間,似乎恨多了一些,有時是莫名其妙的恨。這已經到了沒事找事的地步了。我不知道這是為什么。你不掃自家的門前雪,那么別人家的瓦上霜,你看看也就夠了,干嘛非要拆了人家的瓦?”作為公眾人物,陳道明顯得頗為寂落。
“讓我自己在吧,讓我這個演員的個性在吧,別讓我跟你一樣、跟他一樣、跟大家都一樣!上大學時我看過劉心武的一篇小說,叫做《我愛每一片綠葉》。里面有這樣的一段話: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死角,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天地。當他沒有妨礙你的時候,不要去撞他,不要去罵他,不要去干涉他。人為什么就要像魯迅說的,非得榨出人家皮袍下的小來呢?非得這樣才覺得特別過癮、特別痛快?”
不要說陳道明拒絕媒體,從另外的角度看,媒體似乎也該反省自己了--對待被采訪者,我們是否公正?
不過,與陳道明的聊天,的確有禁區,那就是他的個人生活。
“我覺得,中國人喜歡磨砂吧,我們不是一個透明的民族。這也不是簡單地保護隱私,我沒有什么隱私。主要是個人生活就如同我們戴的手表,很規律,也沒什么特別,所以就沒很必要說了。”
陳道明在很多地方,都保留著傳統中國人的普遍性格,這一點,他自己似乎并不知道。
克制是一種習慣
陳道明一根接一根地續著他的“萬寶路”,他被包在了自己制造的煙霧里,這煙霧繚繞著,我下意識地感到了什么:一個成熟的男人,是不是都很克制?
“我是一個嚴格按照自己邏輯生活的人。這個邏輯不用設定,是習慣。比如某人不愛吃魚,根本不用克制。魚端上來,他肯定不吃。我確實沒有克制。克制是欲而不做,本來就不欲,也就不去做了。”
沉吟了片刻,他又補充:“如果說對某些事有克制,我覺得這是一種理智下的習慣。就像吸毒,當你吸了并上癮時,就離不開它了;但你不吸,就沒事,久而久之,也就成了自然。成了自然的東西是不用你費力去克制的。什么東西成了習慣,就好辦了。”
同行的女記者打趣地問道:“你覺得自己是不是很酷?剛才你一進門,很酷的樣子,嚇了我一跳。不過,‘酷’從另一個角度上來說,是自己對別人的一個姿態:拒絕。”陳道明急得有些發笑:“我沒有拒絕啊,你約我,我如期而至;他(攝影師)讓我抽煙,我就抽了。我很配合啊!”
“如果從內心拒絕,我就不說了。也根本不會坐到這里。我大概是一個表里如一的人。”不論陳道明怎樣解釋,我們的女記者還是堅持認為他很酷,而且很有味道。
文化情結
“因為偶然,我成了一個還算說得過去的演員;因為沒有文化,我又夢想成為一個有文化的人,想成為一個錢鐘書、季羨林式的學問家,又苦于無道無能無才,所以便多出了這個所謂的文化情結。”
在西方,武倫·艾德被稱為最有學者氣質的藝人。而在中國,陳道明的文人氣質也常被人稱道。可陳道明卻反復申明自己“沒文化”,這種說法聽起來很“反常”。
“我們那一代人,拋開自學的部分,其實我們的程度才是小學生。這個無須忌諱。現在再怎么讀書,都是一個被動的詞,叫作‘追’,叫作‘補’,真的。因為天生缺鈣缺得太嚴重了!”之所以不肯稱自己為文化人,是因為對個中緣由頗有感慨。
陳道明一邊在“惡補”文化,一邊在為文化的蛻變痛心:“現在,寫書甚至寫信都變成了一小部分人的事了。筆干什么去了?文字干什么去了?更多地變成職業工具了!記者在使用文字,企業文案在使用文字……可是連情書現在都沒人寫了!數字呢?現在除了記電話號碼和數錢以外,其他也很少被人使用了!我有一種情結,挺喜歡中國的古老文化。當初文字改革,我就想不通。你憑什么簡化?而且一律不許在招牌上使用。為什么要跟我們自己的傳統文化較這么大的勁啊?”
“如果有個意外使你突然‘退休’了,不能再做演員了,你會選擇歷史研究作為職業嗎?”“我會選擇休息。我喜歡我的個人空間。我依然會對歷史感興趣,但不會轉行研究歷史。專家太多了,用不著我。”
(來源:《中華文摘》2003年6月號,原摘自《時尚名流》,文/辰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