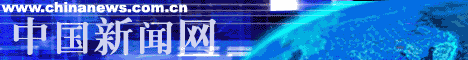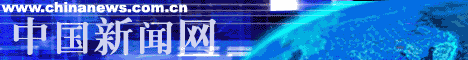直到電視連續劇《空鏡子》問世以前,萬方還是個名聲與實力不太相稱的女作家。雖然已頗具實力,名聲卻不大。萬方總像套中人一樣封閉著自己,在20平方米的寫作間里任思緒馳聘,卻少與外界的熱鬧場有什么交流。其實,她早在十多年前就拿過電影“金雞”最佳編劇獎。
是《空鏡子》在全國的熱播,讓很多人知道了《空鏡子》的作者萬方原來是曹禺的女兒。而這一年正是萬方“知天命”之年,一個經歷已經豐富而精力仍然旺盛的作家。
也許是父輩的名聲太大了,作為中國話劇界泰斗,曹禺的名氣已不需要任何形容詞了。而萬方從記事的那一天起,在父親身邊就如同一個小公主,總是被人們寵著。
可能是曹禺在話劇領域里已攀上了頂峰,也可能是22歲便以《雷雨》震驚天下而解放后再也沒有突破的苦悶,當然更可能是50年代以來文藝界人士一直如驚弓之鳥,使曹禺希望女兒成為一名科學家和醫生,不愿培養她再去當個作家。
但曹禺不得不承認潛移默化的力量,同時還有天性。他發現萬方小時候對事物有種獨特的表達方式,她看天上的烏云,會琢磨出種種鬼怪的影子,從墻壁的水跡中她能找到公主、國王、神仙,能和童話里的形象對上號。她跟著父親去看《雷雨》,看著看著她哭了,曹禺以為她是被響雷聲嚇哭的,其實她是被悲劇情節打動。
她特別喜歡寫詩,上幼兒園時居然能寫短詩,那詩句是大人想不出來的句子。萬方被父親帶到人民大會堂,熟練地背誦了一串毛主席的詩詞:“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一位氣宇軒昂的老人聽罷鼓掌并與她握手,她看著這個人面熟,曹禺告訴萬方:跟你握手的就是周總理啊!十多年后,就是在這個大會堂外,萬方在“四·五”清明節上念了她寫的悼念周總理的詩,在場的人都哭了,給她塞條子留地址,希望得到她的詩。
萬方15歲時家庭發生重大變故,“文革”使她父親和全家跌入深淵。他們住的八間房被紅衛兵搶占,她深深摯愛的母親方瑞也在那個年代去世。方瑞是清代“桐城派”創始人方苞的后代,她良好的文化素養被吳祖光稱為“最后的大家閨秀”。母親對萬方的影響并不亞于大名鼎鼎的父親,萬方在幼兒園作的小詩都被母親抄錄在小本子上,直到她離開人世前還保存著。母親的去世給萬方的打擊極大,30年的時間過去后,她還常在夢中與母親攀談,還希望來世再作母親的女兒。
17歲時,瘦小得還像十三四歲女孩的萬方便到吉林扶余插隊,她在田頭常常有被風卷起的感覺,有時餓極了便到老鄉家要點雜糧與咸菜。回憶起那段生活,她說當時的心情還挺愉快,因為畢竟從“狗崽子”、“黑幫家屬”的歧視中走了出來。與她一起干活兒的還有不少勞教的小流氓,她說那時的流氓也講些義氣,對自己犯的錯誤還感到后悔。這段被放逐的生活成了她以后小說中常常使用的氛圍。
沈陽軍區前進歌舞團的顏庭瑞政委也是個作家,他非常崇拜曹禺,認為曹禺是難得的國寶,他冒著風險想為他景仰的前輩做點事,便把萬方從農村調來搞創作。她到基層、到野戰軍去體驗生活,卻只能不差分厘地用作品去詮釋當時的政策。她雖然比后來的知青作家更早地動筆,但恰恰這幾年使她疏遠了知青生活,未能在70年代后期同那些知青作家一同崛起。
直到80年代初,她才正經開始創作。她為曹禺改編電影劇本《日出》,改名著是件費力不討好的事,幸而她有著與曹禺的父女關系,可以同父親深入交流。曹禺發現女兒的感覺很靈,不僅改編得很有效率,而且讓當代的青年人看得也很過癮。《日出》獲那一年“金雞獎”最佳編劇獎。
曹禺的作品是一個寶庫,萬方愛父親,也愛父親的作品。身為中央歌劇院編劇的萬方又嘗試用歌劇形式改編《原野》,對此曹禺是很擔心的。因為,《雷雨》多次被改編為影視作品,卻遠沒有達到話劇的水準,而歌劇與話劇藝術形式上相差更遠。但萬方對原作進行了濃縮,壓成四幕歌劇,而人物與感情乃至動作都在,加上她的唱詞寫得好,既是人物的,又高于人物的,作曲家拿到唱詞就說:“我的音樂已經有了。”這個歌劇在中國演出成功,又在國際一流的美國肯尼迪藝術中心艾森豪歌劇院上演,萬方應邀出席首演。這個劇耗資100多萬美金,導演是馬里蘭大學音樂系的主任里昂梅杰,被美國稱為“中國人的戲,美國人的制作”。入場券售價高達129美元一張,但十一場演出票還是銷售一空。這是萬方又一次成功,但她把榮譽更多地給了作曲,她說:“歌劇畢竟是屬于作曲家的。”
萬方并不是吃父親老本的作家,她最喜歡寫的是小說。她的幾個中篇小說《在劫難逃》、《殺人》、《未被饒恕》、《珍禽異獸》引起了文學界的關注。但她又很實際,她感到寫小說養活不了自己,她不得不經常涉足電視劇。她知道寫電視劇要占去她不少時間,而且寫多了使寫小說的感覺都受影響。但她畢竟生活在現實中,她不得不變得世俗些。
她父親雖然是大師級人物,但80年代后期老人過得很拮據。有一年春節中國劇協補助了他一千元,萬方也給老人送錢,多病的曹禺才過得不算狼狽。只是后來隨著版權法的實施,香港買了他的演出版權,女導演李少紅買了改編《雷雨》的版權,才使曹禺真正過上小康日子。萬方不愿自己的晚年也像爸爸這樣,她要趁年輕把錢掙足,要沒有后顧之憂地寫小說。
萬方寫了幾十集電視劇,拍完后她基本沒有看過,她說好壞都是導演的事。只有一次例外,那是根據真人真事寫的《牛玉琴的樹》。為這個劇她去陜北采訪了牛玉琴,她驚嘆在這荒漠的黃土地上,一個普通的女性農民會用怎樣堅忍不拔的精神,在離家15里的地方種下2萬畝樹。在采訪中,萬方發現牛玉琴的腰間總是掛著丈夫留給她的小鈴鐺,種樹是他丈夫生前的遺愿。她丈夫得了骨癌,在醫院鋸下一條腿,她把丈夫的腿留好,只是丈夫死后才同遺體一同埋掉。丈夫一直支配著她的生命和理想,使她這個小人物做出驚天動地的事。萬方寫劇本幾乎是一氣呵成,播映后反響很強烈,有關部門評價,看來主旋律也可以寫得很好看。牛玉琴成了英雄,幾次來北京作報告,總忘不了問候萬方。萬方卻以知心朋友的身份勸她找個男人。
萬方和曹禺既是父女,也是朋友。作為一個大戲劇家,曹禺教育孩子的方式也是獨特的。小時候萬方被父親帶去游泳,膽怯的萬方進水后便抓住池邊不松手,曹禺卻按住她的頭往水里扎,嚇得她嚎啕大哭,曹禺卻哈哈大笑。萬方學騎自行車時,年過半百的曹禺扶著車在后面跟著跑,他不時撒手讓女兒摔個跟頭,后來撒手也不摔了,萬方的車算會騎了。哪怕講故事,這位大師也頗講究戲劇結構。他讓萬方當故事中的三公主,萬方妹妹當四公主,講著講著三公主變得又狡詐又懶惰,萬方大聲抗議:“三公主是曹禺!”曹禺把女兒逗急了很是開心,但接下去三公主變得既善良又能干。這種刻畫人物的起伏也給了萬方很深的印象。
萬方很理解父親,自從母親去世,她知道父親內心深處的孤獨,為此她很感激她的繼母李玉茹,并且親切地叫她媽媽。李玉茹的女兒李莉是導演過《楊乃武與小白菜》、《上海一家人》的名導,她和萬方本來是很好的合作對象,但一南一北,始終沒有機會。曹禺對女兒的個人生活也特別理解,萬方婚姻曾有過一次變化,她現在的丈夫程世鑒也是一位劇作家。曹禺當初擔憂的是婚變對可愛的小外孫成長不利,但后來知道這種擔憂是多余的。曹禺深情地寫下:“萬方有個兒子,也是圓頭圓腦,很聰明。在兒子身上,她這個母親可是花費了不少精力和時間,也嘗到了不少痛苦。我不想談孩子的婚姻、感情,因為這是他們自己的事。”
曹禺的晚年疾病纏身,一直住在醫院里,當年充滿著睿智、思辨與幽默的人被歲月消蝕成這樣,萬方為此寫道:“我注視著爸爸,同時,我能感到他的夢。此刻,他的一生就像夢境一樣,既真實又虛幻。他看見許許多多的人和事,他有愿望把這景象告訴我們,可是很困難。于是,在很多時間里,他孤獨地呆在夢里……”萬方深知父親內心的痛苦,她不管多忙,三天兩頭便去探望父親。曹禺只有通過女兒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他會像小孩子似地問萬方:“今天給我說點什么呀?”曹禺的記性越來越差,對每天打針送藥的護士常常張冠李戴,卻不時講出大師的妙語,他對萬方說:“上帝安排得多妙啊,我們老人讓年輕人受累,小孩也讓人累,可是他可愛啊,怎么看怎么可愛。老人就不同了,丑,沒有一點可愛的表演,上帝把你的丑臉畫好了,讓你知道該走了。”萬方安慰父親:“你也可愛呀!”曹禺無奈地笑笑:“你是我女兒,沒有辦法。”
曹禺晚年最感痛苦的是,他二十出頭就名震海外,被西方的同行稱為“中國的莎士比亞”,但在壯年后他的作品很少,而且失去了早年的光彩。這當然不是曹禺一個人獨有的現象,茅盾、巴金、老舍、沈從文都不同程度地經歷了,但一直活到近21世紀的曹禺生命的最后幾年愈發傷感,他曾痛苦地在病房里大喊:“我痛苦,我要寫一個大東西才死,不然我不干!我越想托爾斯泰越難受。”此時的萬方是他惟一可以傾訴的對象,他的家屬中只有萬方一個人懂創作,他把萬方視為生命和事業的延續。曹禺在病房內看了萬方創作的《牛玉琴的樹》,第一次放開了表揚女兒一次:“小方子你能行,能寫出大東西。”
作家出版社要出萬方的小說集《和天使一起飛翔》,非常希望曹禺寫點東西。此時的曹禺身體十分虛弱,寫一個字都很費力。他顫抖著手一筆一劃寫道:“在我的女兒里,萬方是比較像我的一個,所以她成了寫東西的人。她寫的東西我看過,小說《殺人》我覺得有力量,給人思索。我曾擔心她會是一個比較專注自己內心的作者,現在我不擔這個心了,她能夠寫完全不是她的東西,極不相同的人和生活,而且是那么回事兒。可以說她具有創作的悟性和本領了。”曹禺對女兒的愛體現在毫無拔高、偏愛的期望中,這位為中華民族留下堪稱諸多瑰寶的文化巨人用最后的幾百字告別了文壇。在這之后的幾天,老人在沉睡中結束了他燦爛的一生。
(來源:《中華文摘》2003年6月號,原摘自《人物》,文/金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