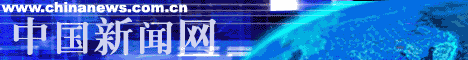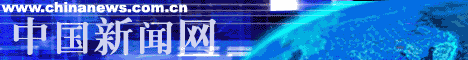作為前百花獎影后,陳沖已在好萊塢闖蕩近20年。從《大班》到《末代皇帝》到《天與地》,她一步又一步地奠定了自己在好萊塢的地位。和國內的情況一樣,她走上演而優則導的道路,從《天浴》到《紐約的秋天》,一位演員出身的中國女導演能獨立指導當紅明星拍片,這在好萊塢是絕無僅有的。
陳沖一直在享受電影帶來的快樂。這次回國,她主要是為了拍侯詠的《茉莉花開》。在電影里,她和章子怡演一對母女,先后作為三個不同時期的母親出現。除了拍這部戲,她還忙里偷閑,奔赴北京和池莉見面,買下了中篇小說《驚世之作》的電影改編權。現在,她的導演計劃上已經至少有3部電影了。
年紀輕輕就走到了頂端,下一步怎么走呢?哪個方向望過去一定都是下坡
南方周末:在最紅的時候,你怎么舍得放棄名利選擇去美國呢?
陳沖:那是你們在從外面看啊,我在里面啊。我當時只是一個孩子,想要讀書啊。我并沒有覺得名利能帶來多大的快感啊。我學的是外語,我們家庭都渴望正常,我一不小心就成為電影明星,拿了全國第一個影后,他們都覺得不正常,不正常就不舒服。當時我們大學演出隊到外面演出,在西安的時候,有幾次整個大街的自行車都踩亂了,人都弄傷了去醫院,這些場面很可怕,也讓我覺得不正常。
當時我就想,我并沒有做過什么大的事情啊,在出名前的我和出名以后的我都是同一個人,并沒有什么改變,怎么就變熱了呢?而且那么多人圍著崇拜我,我不知道自己究竟付出了什么。特別不自然,我沒有心安理得過。我覺得這是一件完全沒有理由的事情,不正常,特別不自然。
南方周末:那時會不會也有一些虛榮心呢?
陳沖:有,虛榮心也許有一點滿足,但是很快這種不安不快樂就超過了虛榮心的滿足,而且不踏實。我是那種蠻知足的人,相信一分付出就有一分回報,可是那個時候,一切都看起來那么怪。所以有出國的機會,我就去美國了。
到美國讀書,可能是當時一種下意識的選擇,但是按照我現在的成熟回想那個時候,也許還是有一種害怕———年紀輕輕就走到了頂端,下一步怎么走呢?哪一個方向望過去一定都是下坡,這樣想的話就走掉算了。
南方周末:你去美國很多年后,才真正進入電影圈。之前你主要在做什么?
陳沖:剛出去也和別人一樣,上學,打工,在餐館刷碗,沒有什么不平衡的。當時的環境都是這樣,而且我也沒有覺得會在美國刷一輩子碗啊。我覺得一個人不經歷這樣的生活也就沒有創作的來源了,我挺高興的受這些苦。
第一學期是出國前就安排好的,第二學期我就轉學了,對自己是一個很大的鍛煉,什么都靠自己。一開始是在紐約大學,大學不需要選專業的,大家都上普課,后來我選擇的是戲劇,轉到加州大學后,選的基本都是電影制作方面的課,不過也不是特別規范,選了很多宗教理論等各樣的課,只要自己有興趣,就去上課。當時這個大學有一些中國教授,也可以替我安排獎學金什么的,但是課余時間里也打工,因為學費蠻高的,當時他們沒人看過中國電影,沒有人知道我,對我沒有特別優待。
南方周末:那時在美國讀書有多困難?陳沖:當時也很困難的。在學校讀了3年以后,開始了第一部戲,然后又斷斷續續在讀,后來差不多我快讀了10年才畢業。其實我應該早拿到學位的,因為我選了很多與專業無關的課程,我的學分遠遠超過拿學位所需要的分數,因為我在拍戲嘛,所以現在回過頭,我還是很驕傲。因為我學習就是因為自己喜歡,畢業和我的專業和我賺的錢做的事毫無關系,沒有任何幫助。
出國學習是我的初衷,我把它變得特別有象征意義。生活本身是沒有意義的,意義是我們賦予的。
我當時肯定很不愉快,剛剛來到美國就挨了一棒子,但是那么多年前的事情,我的記憶不是那么有質感了。
南方周末:《大班》讓你受到不少國人的指責,在國外的評價也有些負面,獲得當年金草莓獎“最差女演員”、“最差新人”兩項提名,那時候的境況不太好吧?
陳沖:那是一個玩笑獎,不是什么正式的獎,有一幫人在那里看電影玩出來的一個獎,而且等《大班》上映,我已經在拍《末代皇帝》,已經進入下一個階段了。我當時肯定很不愉快,剛剛來到美國就挨了一棒子,但是那么多年前的事情,我的記憶不是那么有質感了。
也許有一點壓力,對我的家人大一些,我的父母、姥姥,可能他們在國內,感受到的壓力就比較具體一些,比較大一些。
南方周末:你是中國的影后,但到了美國卻在演技方面遭到指責,這種心理上的落差你是怎樣克服的?
陳沖:你要生活得好,就必須有生產力,這就是對一切的回答。有苦的時候就必須承受,把眼淚吞下去。我有很多脆弱的時刻,我非常不愛哭,尤其是在眾人面前,能夠控制自己的感情,我女兒這一點也非常像我。
南方周末:《末代皇帝》是在美國生涯的一次轉機嗎?為什么貝托魯奇會找到你呢?陳沖:應該是吧,其實在拍《大班》之前,專門為貝托魯奇找演員的人就看上我了。當時,我在為另外一部電影試鏡,我最終沒有得到那個角色,但他當時就看中我身上的某些氣質了,記住我了。他對貝托魯奇講,你要的這個婉容,沒有他人,就是陳沖了。那個時候,每出戲你作為一個新人,都要爭取,尤其是重要的角色,他們通常會安排很多角色讓你當場排演,就這樣考演員。我被他們考過,所以他對我的印象很深。
我甚至不怕去機場擦皮鞋,雖然我對皮鞋沒有感情上的投入,如果是為了謀生可以做別的。
南方周末:《末代皇帝》之后,有5年時間,你似乎轉向了電視圈,為什么?《雙峰》在你這段時間里占據著怎樣的地位?
陳沖:我演過很多電視劇,每個劇和國內不太一樣,都是一本一本往下寫的,在兩本之間都會有一些客串戲,我在這些電視劇中間基本都是客串戲。
《雙峰》確實對我在美國的幫助非常大。美國人在大街上認識我的話,仍然是因為電視劇《雙峰》,它使我能夠真正被美國觀眾所接受。到現在為止,我女兒去上學,她的老師現在還會提起《雙峰》。一般試演都是在辦公室,但是那天沒有給大衛·林奇演過戲,他直接就決定了由于我演。
做到拍《天浴》之前,我突然就膩了,因為我非常愛電影,對拍平庸的戲沒興趣了。我甚至不怕去機場擦皮鞋,雖然我對皮鞋沒有感情上的投入———如果是為了謀生可以做別的。
直到后來拍《天浴》,自己寫自己導,賦予它意義,我才回到電影上來。
南方周末:1998年,你一人身兼制片、導演、編劇,拍了《天浴》,投資人為什么放心把這么多重要的職位交給之前在這些方面沒有什么經驗的你呢?
陳沖:我覺得真正想要的人都是能夠得到的,《天浴》的劇本是我先寫的,然后嚴歌苓幫我潤色,反正都是自己在拼命在做,后來沒有找過任何美國公司,而是把劇本拿給一些個人看,終于找到100萬美金,就開始拍這部電影了。
南方周末:在《紐約秋天》里指揮理查德·基爾和薇諾娜·賴德這樣的明星,對你來說會不會有壓力?
陳沖:工作之前有些壓力,但是工作開始以后就沒有了,每天面對的是具體的工作,和演員的合作整個工作過程還比較愉快,就是制片的干擾比較多一些。電影這個東西,跟任何生意一樣,不是說你認為能夠賺錢就能夠賺錢的。
南方周末:對今天的中國電影人來說,這些機遇還存在嗎?
陳沖:當然,而且比我們那個時候要好多了,整個世界現在對中國的認識不同了,而且像李安、吳宇森都證明了他們在市場上的成功,讓美國人意識到,中國人拍的電影也是可以有好票房,賺到大錢的。電影工業的保守主要是因為市場,他們認為也許這樣的人種不能得票房,如果是證實你是可以得到票房,那么就漸漸松弛了,但是他們是否能夠寫出特別棒的角色,我依然懷疑。不過,對中國電影人來說,現在的機會比以前多了很多。
南方周末:你對“文化大革命”那段歷史念念不忘,是不是你比較熟悉,另外在國外這樣的電影比較討巧?
陳沖:不!“文化大革命”這段歷史太屬于全世界了,太不應該被拋棄避而不談了,這是人類的一個事件呀!
像我這一代人,或者比我大10歲的人,他們的感受永遠會記得那些曾經發生過的事情。人的生活是由人的經歷所決定的,“文化大革命”這段歷史永遠留在了我們這一代人心中,它是我們的青春,是我們揮不去的情結,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電影的主題不是我能夠決定的,只能說它選擇了我,這份責任心也是在我的血液當中,我們的人生體驗和經歷的事情永遠留在我的生命里,感動我打動我,讓我感動讓我流淚讓我興奮,就是這樣,對我們這代人來說,就是這樣的。而對于另外一代人來說,她們所經歷的生活可能是另外一樣的,比如衛慧的小說,她就是對她那一些年輕人的生活記錄,他們的人生經歷和掙扎和我們完全不一樣,這是由于生活的不同經歷所造成的,我們沒法取代對方的作品。
來源:南方周末 作者:張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