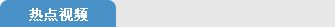- 《中華文摘》文章:俞飛鴻:我是這圈的邊緣人
(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黎巖
昔日北影校花花了8年的工夫拍出了自己心中的愛情片《愛有來生》,卻堅決不談關于自己愛情生活的一切。
俞飛鴻根本不像這個圈子里的人,她出生于杭州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當年在美女如云的北京電影學院表演系被公認為“校花”,是“美女中的美女”。俞飛鴻喜歡可愛的狗,男生們以遛狗為借口約校花出來,一時附近狗市價格飆升。
如今的“校花”卻把人生中最精彩的8年拿出來,精心打造了一部電影,在同時代女星忙著享樂、鬧緋聞的時候,她的日子在對自己的挑剔和苛求中度過。
2001年,俞飛鴻買下小說《銀杏銀杏》的版權,開始籌拍電影《愛有來生》。打造劇本用了4年;找投資選景用了兩年的時光;2007年3月開始拍攝,10月拍攝完成,用了7個月;后期制作用了一年。
2009年,電影定于七夕上映,但是因為俞飛鴻不滿意拷貝,不得不重新制作,該片又拖到9月初上映,但在七夕當天在北京首映一場。
發(fā)行方說這會導致重大損失,但俞飛鴻堅持道:“這個效果真不是我要的,我電影的畫面是非常美麗的。我希望觀眾能在影院里真正享受到觀影的樂趣,真正領會到我對這個電影付出的真情。”所以,她寧可自己掏腰包重新拷貝。
2009年是娛樂圈的特殊年份,此圈將炒作的功力逼到了改革開放后的白熱化階段:人們可以炒分手,炒結婚,炒跟導演不合鬧停工,全為了一部戲的票房。
有人炒跑調,有人炒恩怨:“章子怡和范冰冰交惡”傳聞鋪天蓋地。章子怡在南京記者見面會上被指責遲到時飆淚。有網友說,哭誰不會啊。類似新聞始終占據(jù)著各大媒體的顯著位置。《愛有來生》中規(guī)中矩的宣傳被淹沒其中。
有記者問俞飛鴻,面對同期上映的《非常完美》、《機器俠》等諸多影片的競爭是否有壓力,俞飛鴻說:“我很釋然,如果我對自己的電影沒有信心,也不會堅持到現(xiàn)在。”當被問及《愛有來生》的賣點時,俞飛鴻回答:“我不是一個商人,不懂什么賣點。這部電影所堅持的就在于把本身最大的真誠奉獻給觀眾。”
在一次電視專訪中,主持人要俞飛鴻談談自己的愛情生活,她什么都沒說。京城作家趙趙揭露,俞飛鴻的最大特點是愛打聽周圍朋友的八卦,但是從來都不說自己的任何事情。
俞飛鴻說:“生活越平淡,我就越踏實。”
我是這圈兒的邊緣人
《新世紀周刊》:第一次做導演很難吧?
俞飛鴻:以前沒遇到過這么龐大的工作,每個階段都會遇到困難,但這是我自找的,我不做就不會經歷這些。
《新世紀周刊》:電影拍攝之初為什么放棄宣傳?
俞飛鴻:不想被(媒體)打擾,想安安靜靜地完成我的工作。
《新世紀周刊》:目前都在宣傳電影本身,這樣真行嗎?
俞飛鴻:我現(xiàn)在沒有男朋友,也沒有結婚,真沒什么可說的。沒有的東西讓我造出來會讓我笑場,我配合不到,無法參與,演不下去,我沒法做我做不來的事情。這是我的性格。我奉行自然交往的生活態(tài)度。我覺得觀眾不需要我去討好他們。觀眾需要我真誠地去做作品,跟他們分享。我認為那么多國家大事兒呢,應該沒人愿意去關心我的小事兒。
《新世紀周刊》:那票房怎么辦?
俞飛鴻:我只能身體力行地配合宣傳關于這部戲的一切,這個戲凝聚了太多人的心血,我必須對他們負責,所有的通告,來了就接了,什么都不問。其實就我來說,采訪超過五個我就受不了了。我唯一的要求是不做娛樂節(jié)目,不談八卦。
《新世紀周刊》:怎么看待不炒作不成活的娛樂圈?
俞飛鴻:這是一種畸形營造,有人愿意這樣做就這樣做吧,我沒有什么可評論的,我只能做我熟悉的。
《新世紀周刊》:你跟圈里的人不一樣。
俞飛鴻:我不覺得自己是這個圈兒的,我比較邊緣吧。我很滿意我現(xiàn)在的生活方式,工作之余自己在家一待,在房間里來回走走,晚上睡覺用書來催眠,特好。
《新世紀周刊》:你在美國的時候也沒談戀愛嗎?
俞飛鴻:談戀愛我也不告訴你。
《新世紀周刊》:你2006年時主演了一部電影《千年敬祈》,這個電影還在西班牙獲得了“金貝殼獎”,你怎么從來沒提到過?
俞飛鴻:因為沒有人問啊。
《新世紀周刊》:你在《千年敬祈》中大多是講英語,你的英語特別棒,怎么平時也不在公眾面前飆一下?
俞飛鴻:我對面坐的不是外國人。
從觀眾的角度拍這部電影
《新世紀周刊》:一開始劇本讓比較有名的編劇寫,后來你又自己寫了,他們寫的東西什么地方讓你不滿意?
俞飛鴻:他們寫得非常好,但拍出來是另一部電影。我要的劇本會模糊淡化具體的大背景,主要講情感。
《新世紀周刊》:你的電影屬于什么風格?
俞飛鴻:我也不知道,是自然表達。
《新世紀周刊》:你心目中好的電影應該是什么樣的?
俞飛鴻:故事簡單,情節(jié)復雜。
《新世紀周刊》:你最在乎自己電影里的什么東西?
俞飛鴻:情感純粹,觀眾看電影時想到了自己的經歷,回憶起曾經的情感,從而不會被歲月模糊忽視掉,更加珍惜身邊擁有的東西。這包括親情、愛情、友情。
《新世紀周刊》:為什么《愛有來生》是從觀眾的角度去拍攝,觀眾很難討好吧?
俞飛鴻:其實我說的是心態(tài),我是以觀眾心態(tài)去拍電影,我不會把自己放在一個教育者或者先知的位置上去完成電影,這是居高臨下的做法,我不認同。我覺得觀眾與我在智商和智力上是平等的,甚至比我更強。我僅僅是做了一個搜集和表達的工作。觀眾應該不是為電影感動,而是為自己。
這部電影不會太女性
《新世紀周刊》:編劇、導演、原著都是女性,會不會讓電影局限在女性思維里?
俞飛鴻:首先是人的思維差異,然后才可能談到性別上的差異,比如李安導演的片子,拍得比女性還細膩,還糾結。這和個性有關,和性別無關。大氣磅礴也不是男人的專利。作品應該以創(chuàng)作者個體來區(qū)分,而不是性別。
《新世紀周刊》:目前大陸70后女導演只有你和徐靜蕾,看過她的電影嗎?
俞飛鴻:看過,我覺得她比許多男導演都強。她在表述上很流暢,很完整、很明確地知道自己在講什么,這很難得,勝過很多男導演。有些男導演拍了很多片子還不會講故事,不能表達清楚,我看完他們的電影都不知道他們想說什么。因此,我覺得外界對徐靜蕾的批評很苛刻。
《新世紀周刊》:會不會覺得這個行業(yè)就是男人的世界?
俞飛鴻:本身就是,以后也是。這個真談到性別差異了,雖然現(xiàn)代社會已經很多元化,但將來也還是會以男性為主,這沒有什么可憤憤不平的。比如帶兵打仗的很少有女將軍,這就是生理心理因素決定的。導演其實是個體力活,女人、尤其是有了小孩之后的女人,很難精力集中,男女在體力、精力、構造上就有區(qū)別,女性比較感性,會容易分散注意力,男性則容易集中在一件事情上,這是大腦的區(qū)別,沒有辦法。
《新世紀周刊》:怎么處理和你共事的男人的關系?
俞飛鴻:氛圍營造得非常好,我們一起感受整個故事,然后到現(xiàn)場把所有的戲走一遍,所有的人都往一個方向走,慢慢大家的心就會凝聚,最后建立了對我的信任。信任感非常重要,沒有信任感會影響氣場。我有時也會按照他們的方式來改動,比如臺詞什么的,最后形成一種默契。
《新世紀周刊》:做這個電影的時候,能真正幫到你的都是男人,比如王朔、徐克、姜文……
俞飛鴻:這個行業(yè)本來也是男人做得多。其實影片后面的感謝名單里好多女人呢。
《新世紀周刊》:愛比較重要還是做事比較重要?
俞飛鴻:快樂最重要。(摘自《新世紀周刊》)
-
----- 精選 -----
我國實施高溫補貼政策已有年頭了,但是多地標準已數(shù)年未漲,高溫津貼落實遭遇尷尬。
Copyright ©1999-2024 chinanews.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