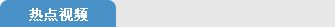- 錢學森晚年有妻陪伴不寂寞 研究“吃”也很認真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熟悉錢學森的人都說,“錢老晚年不寂寞,因為他身邊始終有蔣英”
本刊記者/李邑蘭
11月1日,深秋的京城驟降大雪。這是錢學森辭世的第二日。來自北京市氣象臺的消息稱,今年的第一場雪罕見地提前,是北京自1987年以來最早的一場初雪。
趕來吊唁的人們不約而同地念叨著,這場雪是為偉人的離去而準備的。前來吊唁的78歲的范良藻是錢學森1956年在中國科學院招收的第一批也是唯一一個物理學研究生,自1958年畢業,他們已經闊別50年了。
航天大院8號院深處一棟相對獨立的三層紅磚小樓,是錢學森生活了50年的家,門前兩側已經擺滿了社會各界人士送來的花圈。晚年臥病在床的錢學森,絕大多數時光就在這幢三層小樓里度過,除了身邊的秘書和家人之外,他很少與外界直接聯系。而中科院力學研究所研究員范良藻與老師錢學森這50年間,大都是通過書信往來的。
總裝備部的相關負責人介紹, 11月1日上午已經陸續有200多名社會各界人士自發趕來為錢老送行,這其中包括錢學森的學生、老鄰居、老同事、北京各高校的大學生等。吊唁從11月1日開始,連續6天,每天早上8點半至11點半,下午1點半至5點向公眾開放。
“追悼會暫定11月7日在八寶山舉行,一切都由中央統一安排。”錢學森的兒子錢永剛教授向媒體宣布。對于錢家而言,錢學森的葬禮已不完全屬于錢家,“這是國家大事。”
不寫書,免得活著就后悔
“我們是近在咫尺,卻又遠在天涯啊!”今年84歲的王毅丹向《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感嘆。
曾在航空航天部辦公廳工作的王毅丹,是離錢學森最近的鄰居。錢家所在的三層紅樓共有兩個單元,四單元只住錢學森一家人,三單元住著六戶人家,王毅丹家是其中之一。
“錢老剛回國時,住在中關村。50 年代末搬到這里來之后,就再也沒有搬過家。”86 歲的老同事亓英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亓英德住在航天大院五單元,與錢學森已經做了50年的鄰居,亓退休前的職務是航天工業部財政局局長。
這期間,領導曾多次動員錢學森搬家,表示會按全國政協副主席的級別給他蓋一棟小樓,可他不要。上世紀90 年代,錢學森的秘書涂元季動員錢老搬家:“和您同船回國的人大部分都當上了院士,院士現在都搬進了新居,比你這老房子好。”涂元季還將已建好的小樓照片拿給他看,“您若住進這樣的小樓,可以在院內曬曬太陽,對身體有好處。”錢學森卻回答:“我在這里住慣了,你讓我住進小樓,我渾身不自在,能對身體有好處嗎?”從此人們再未提搬家的事。
老鄰居們都對錢學森早年的狀況印象深刻。家住航天大院34單元的老人劉小芳至今仍對10年前見到錢學森時的情景記憶猶新。每晚七點,吃完晚飯,劉小芳總愛到大院遛遛彎,“那時錢老身子還硬朗,也常出來遛彎,每次見到我們,都會主動打招呼,樂呵呵地和我們說話,非常平易近人。”她記憶中的錢學森,經常穿著藍色或灰色上裝,綠色的軍褲。
7年前,王毅丹搬到了航天大院居住,成了和錢學森離得最近的鄰居,“但這并沒能讓我更多地了解錢老”。此時的錢學森,因為身體原因,已經很少出門,漸漸遠離了鄰居們的視線。王毅丹表示“近七八年來,我只見過錢老一兩次。”
王毅丹也有遛彎的習慣,這些年每每經過錢家的時候,“窗戶多是半掩著的,窗簾緊閉,看不到里面。”樓外站著兩名警衛日夜守護著,“這也讓我們很多鄰居只能遠望,而不敢登門拜訪”,王毅丹說。
在前來吊唁的人中,有一位名叫陳兆武的年輕人,7年前,他曾是錢學森家的警衛排長,但也沒有進過小紅樓。在他當勤的兩年,只見過錢老兩次,都是陪同他去解放軍總醫院檢查身體。“當時錢老的健康情況并不是很好,已經癱瘓在床,吃飯喝水都要別人喂食。”
錢家從來不缺“貴客”登門。溫家寶總理最近一次看望錢學森,是今年8月6日,這是溫家寶近年來第四次看望錢學森。80年代中后期開始,溫家寶就經常和時任中國科協主席的錢學森一起研究工作,并多次書信往來。而此前,江澤民也曾于1995年、1996年、1999年和2000年先后四次到錢學森家中看望。
“每到這時,院子外就會聚集一大批人,隔著小區馬路張望。”王毅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大家會好奇地猜測領導們又在和錢老討論什么重大問題。
錢學森一生做人有四條原則:不題詞;不為人寫序;不出席應景活動;不接受媒體采訪。
1950年,錢學森曾跟一個加州理工大學的學生說:“人在臨終前最好不要寫書,免得活著時就開始后悔。”僅見的關于錢學森的傳記,是美國已故作家張純如的著作《中國飛彈之父─錢學森之謎》,而該書在大陸幾乎不可得,這就更加深了晚年錢學森在公眾心目中的神秘感。
我國實施高溫補貼政策已有年頭了,但是多地標準已數年未漲,高溫津貼落實遭遇尷尬。
Copyright ©1999-2025 chinanews.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