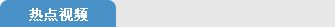- –§˙ó:”⁄µ§≤Ω÷‹Ω‹Çê∫Ûâm ∞—ǘΩyŒƒªØä ò∑(”fiò∑)ªØ


°°°°ÿM»›”⁄µ§‘ŸŒ€«f◊”
°°°°°™°™ûÈÌn√¿¡÷≈˙”⁄µ§“ªfiq
°°°°-–§˙ó
°°°°÷‹Ω‹Ç굃∏Ë£¨‘Æ”√ǘΩyŒƒªØ‘™Àÿ£¨’˝»Á∆‰‘Æ”√¡˜––ŒƒªØ‘™Àÿ£¨∆‰◊⁄÷º÷ª‘⁄ä ò∑£¨∆‰–ß”√“≤÷ª‘⁄ä ò∑°£À¸å¶”⁄ǘΩyŒƒªØµƒ“‚¡x£¨≤ª‘⁄∫ÍìP£¨∂¯ «œ˚Ω‚£¨“ÚûÈ‘⁄∆‰À∆ «∂¯∑«µƒ≈≤”√÷–£¨Ç˜ΩyŒƒªØµƒºÉ’˝–‘∫ÕÕÍ’˚–‘±ª÷´Ω‚∫Õ»°œ˚¡À°£ìQ—‘÷Æ£¨Ç˜ΩyŒƒªØ‘⁄÷‹Ω‹Ç굃∏Ë≥™Àá–g÷–£¨÷ª «“ª∑N±ª÷´Ω‚°¢∆¥ŸNµƒä ò∑‘™Àÿ°£”⁄µ§¬ï∑Q°∞Œ“’JûÈ÷‹Ω‹Çê∫Õ∑ΩŒƒ…Ω£¨ƒ≥∑N“‚¡x…œ£¨∏˙Œ“◊ˆµƒ ¬«È « ‚ÕæÕ¨öwµƒ°±£¨Œ“œ‡–≈”⁄µ§‘⁄¥À’f¡À“ªæ‰’Ê‘í£¨“ÚûÈÀ˝ π”√¡ÀÕ¨ò”µƒä ò∑ªØ‘≠Ñt∞—°∂’ì’Z°∑∫Õ°∂«f◊”°∑éß»ÎÆîΩÒ÷–᯵ƒ¥Û±ää ò∑ –àˆ°£
°°°°»’«∞£¨÷¯√˚Àá–gº“Ìn√¿¡÷‘⁄’˛Öfï˛…œ÷±—‘£∫°∞Œ“胫∞Õ¶≥Á∞›À˝”⁄µ§µƒ£¨Õª»ªÀ˝±ƒ≥ˆ“ªÇÄÀ˝œ≤ög÷‹Ω‹Ç꣨fl@œ¬◊”Ω^å¶úÁ¡ÀŒ“œ≤ögÀ˝µƒœÎ∑®°£“Úûȃ„ÃÏÃÏ÷v«f◊”£¨ø◊◊”£¨ƒ„Õª»ª“ªÇÄ÷‹Ω‹Ç꣰ƒ„÷v«f◊”£¨«f◊”≤ª «’f°ÆÃϵÿ”–¥Û√¿∂¯≤ª—‘°Ø£¨ƒ„‘ı√¥œ≤ög“ªÇÄ¥Û∫∞¥ÛΩ–µƒ£ø‘⁄ƒ«É∫≈™fl@“ªÃ◊£°ƒ« «“Ùò∑Ü·£øƒ« «ÎsÀ££°°≠°≠ƒ„fl@√¥¥Û∞—ƒÍºo¡À£¨ƒ„÷v÷¯Œ“ÇÉ÷–á¯Ç˜Ωyµƒñ|Œ˜µƒïr∫Ú£¨ƒ„÷vµΩ√¿åW¡Àõ]”–£øƒ„÷™µ¿«f◊”¿Ô√Ê”–∂‡…Ÿ√¿åWÜ·£øƒ„ºŸ»Á÷™µ¿µƒ‘í£¨ƒ„æÕ≤ªï˛’ffl@ÇÄ‘í£°°±Ìnœ»…˙¥À—‘“ª≥ˆ£¨º¥øñª√ΩÛwπ⁄“‘°∞≈⁄fiZƒ≥ƒ≥°±µƒ√˚Ãñ≥¥◊˜ûÈ”÷“ªÇÄ√ΩΩÈü·¸c°£
°°°°Ìnœ»…˙“‘72öqµƒ∏fl˝g∞l≥ˆ¥À∑Œ∏≠÷Æ—‘£¨∆‰÷–Îm≤ª√‚ÈL’fl∆´º§÷Æ’Z£¨µ´—‘÷Æ’Å’Å£¨¡x÷Æ«–«–°£”⁄µ§“¿»ªπ Œ“µÿ°∞∏fl◊ÀëB°±ªÿë™Ìnœ»…˙µƒ≈˙‘u£¨À˝å¶√ΩÛw’f£∫°∞“ª∞„»ÀƒÍºo¥Û¡À£¨µÿŒª∏fl¡À£¨æÕ»›“◊ø⁄ «–ƒ∑«£¨‘uÉr Ï»Àïr∏¸ «»Á¥À£¨µ´Ìn¿œéü“ª÷±∂º‘⁄’f’Ê–ƒ‘í£¨èƒœ≤ögŒ“µΩ≤ªœ≤ögŒ“£¨¨F‘⁄‘⁄∞l—‘÷–ÃÊŒ“Õ¥–ƒ£¨“ª¸c∂º≤ª◊ˆ◊˜£¨fl@∫‹Îyµ√£¨Œ“ƒ‹∏–”XµΩÀ˚µƒ’\“‚£¨¿œ†î◊”’Êø…ꀣ¨œ£Õ˚èV¥Û◊x’fl≤ª“™ûÈÎyÀ˚°£°±(–Ï¡¶£∫°∂Ìn¿œ’Êø…ꀥۺ“ÑeûÈÎyÀ˚°∑£¨≥…∂ºÕÌàÛ£¨20090314)
°°°°◊˜ûÈ∫Û›Ö£¨Œ“öJ≈ÂÌn√¿¡÷œ»…˙ûÈ÷–ᯌƒªØµƒΩ°»´∞l’π¥Û¡x÷±—‘£°Œ“‘¯”––“‘⁄“ªÌ󌃪تÓÑ”÷–≈cÌnœ»…˙îµ»’œ‡Ãéπ≤ ¬£¨À˚’Ê «“ªÇÄ°∞≤ª ß≥‡◊”÷Æ–ƒ°±µƒ°∞ø…ꀵƒ¿œ†î◊”°±°£µ´ «£¨Œ“ÇÉ≤ªƒ‹“ÚûÈÌnœ»…˙µƒø…ꀣ¨æÕå¢À˚·òÌæïr±◊µƒá¿√C≈˙‘u¥Ú»Îä ò∑ŒƒªØµƒ¿‰åm°£ «“≤£¨∑«“≤£¨Œ“ÇÉë™Æî’J’ʱʌˆ°£
°°°°÷‹Ω‹Çê≈c«f◊”√¿åW
°°°° ◊œ»∞—÷‹Ω‹Çê≈c«f◊”(á¯åW)≥∂‘⁄“ª∆£¨≤ª «Ìn√¿¡÷£¨∂¯ «”⁄µ§±æ»À°£À˝‘⁄2007ƒÍµ◊—Γï°∂√Êå¶√Ê°∑Ω” ‹”õ’flÕı÷æ‘L’Ñïr£¨–˚∑Q°∞¨F‘⁄»´ ¿ΩÁµƒ»À∂º÷™µ¿Œ“ü·ê€÷‹Ω‹Çê°±£¨≤¢’f£∫°∞¨F‘⁄”–∫‹∂‡»À∞—÷‹Ω‹Çê∏˙ǘΩyŒƒªØ嶡¢∆ÅÌÜñŒ“£¨’fŒ“ÇɃ͛pµƒ∫¢◊”∂º»•¬†fl@∑N¡˜––∏Ë«˙¡À£¨»ª∫Ûƒ„‘Ÿ÷v°∂’ì’Z°∑°¢÷v°∂«f◊”°∑£¨ƒ„‘ı√¥ò”≤≈ƒ‹”√fl@∑NǘΩyŒƒªØµƒ∫À–ƒÉr÷µ»•”∞Ìë¨F‘⁄µƒ∫¢◊”£¨Œ“∫‹Ãπ¬ µÿ∏Ê‘VÀ˚ÇÉ£¨Œ“’JûÈ÷‹Ω‹Çê∫Õ∑ΩŒƒ…Ω£¨ƒ≥∑N“‚¡x…œ£¨∏˙Œ“◊ˆµƒ ¬«È « ‚ÕæÕ¨öwµƒ°£°±Ìn√¿¡÷ë™Æî «¬†µΩ”⁄µ§»Á¥À’f∑®∫Û£¨≤≈Æa…˙¡Àå¶À˝ «∑Ò∂Ƶ√«f◊”√¿åWµƒŸ|“…£¨“ÚûÈÀ˚’JûÈ’Ê’˝∂Ƶ√(’JÕ¨)«f◊”√¿åWµƒ»À£¨ «≤ªï˛–¿Ÿp÷‹Ω‹Ç굃°£
°°°°«f◊”µƒ√¿åW£¨◊˜ûÈ÷–á¯π≈¥˙µƒ°∞ºÉÀá–gæ´…Ò°±(–ÏèÕ”^’Z)µƒ∞l‘¥£¨∆‰æ´…Ò¡x¿Ì «òOÿS∏ª…Ó‰µƒ°£æÕ¥À£¨Œ“ÇÉ÷ªø…≈e≥ˆ∆‰∫À–ƒ“™¡x°£«f◊”√¿åWµƒ◊⁄÷º£¨ «°∞≈c‘όԒflûÈ»À£¨∂¯”Œ∫ıÃϵÿ÷Æ“ªö‚°±(°∂«f◊”°§»ÀÈg ¿°∑)£¨º¥“‘Ûw’JÃϵÿ»fŒÔµƒ∏˘±æ°∞µ¿°±(ö‚)ûÈ÷ºöw°£“Ú¥À£¨“ª∑Ω√Ê£¨À˚‘⁄»fŒÔΩy“ª”⁄µ¿(˝RŒÔ’ì)µƒª˘µA…œ≥÷åè√¿œ‡å¶’죨º¥À˘÷^°∞Öñ≈cŒ˜ ©µ¿Õ®ûÈ“ª°±(√¿≈c≥Û‘⁄∏˘±æ…œ «“ª÷¬µƒ)£ª¡Ì“ª∑Ω√Ê£¨À˚”÷÷˜èà“‘ÃìÏo≥Œ√˜µƒ–ƒÏ`†T’’Ãϵÿ£¨èƒ∂¯Õ∏¨F”Ó÷Ê◊Ó…ÓøÃ∂¯ÏoòOµƒ±æÛw°£(°∞ÀÆÏo™q√˜£¨∂¯õræ´…Ò£° •»À÷Æ–ƒÏo∫ı£°Ãϵÿ÷ÆËb“≤£¨»fŒÔ÷ÆÁR“≤°£∑ÚÃìÏo°¢ÃÒµ≠°¢º≈ƒÆ°¢üoûÈ’fl£¨Ãϵÿ÷Æ∆Ω∂¯µ¿µ¬÷Æ÷¡£¨π µ€Õı •»À–›—…°£°±°™°™°™°∂«f◊”°§ÃÏfl\°∑)“¿¥Àåè√¿æ´…Ò£¨«f◊”µƒåè√¿»§Œ∂£¨∑¥å¶øÓ‚µÒ◊¡–fiÔó£¨÷˜èà°∞µ≠»ªüoòO∂¯±ä√¿èƒ÷Æ°±µƒ°∞ò„Àÿ°±µƒ√¿∏–°£fl@ò„Àÿµƒ√¿∏–£¨ «°∞‘≠Ãϵÿ÷Æ√¿∂¯fl_»fŒÔ÷Æ¿Ì°±∂¯≥…£¨“Ú¥À°∞ò„Àÿ∂¯ÃÏœ¬ƒ™ƒ‹≈c÷Ɔé√¿°±°£∫Ü—‘÷Æ£¨“‘◊‘Œ“µƒ°∞ÃìÏo÷Æ–ƒ°±£¨”^’’ÃϵÿÈg°∞Àÿò„÷Æ√¿°±£¨ ««f◊”√¿åWµƒ“™¡xÀ˘‘⁄°£–ÏèÕ”^œ»…˙’JûÈ«f◊”◊∑«Ûµƒ «“ª∑N¬‰åç”⁄»À…˙µƒ°∞ºÉÀÿ°±÷Æ√¿£¨fl@∑N√¿Ûw¨F”⁄Àá–g£¨ «”…÷–᯵ƒÀƃ´…ΩÀÆÆãûÈ¥˙±Ì£¨åçûÈæ´µΩ÷Æ“ä°£(°∂÷–á¯Àá–gµƒæ´…Ò°∑£¨»Añ|éü¥Û≥ˆ∞Ê…Á£¨2001ƒÍ∞Ê)
°°°°÷‹Ω‹Ç굃∏Ë≥™Àá–g±Ì¨Fµƒ «≈c«f◊”√¿åW÷º»§œ‡Æ굃¡Ì“ª∑N ¿ΩÁæ∞œÛ£¨ «Æî¥˙»À∏Òµƒ◊ÓΩK∫¢Õتصƒ°∞«‡¥∫◊‘Œ“°±£¨º¥ «üoöv ∑”õëõµƒ°¢ºÉ¥‚∏––‘µƒ°¢ÀÈ∆¨ªØµƒ◊‘Œ“µƒ ¿ΩÁæ∞œÛ°£fl@ «“ªÇÄ∑«÷––ƒªØµƒ°¢»Œ“‚∏–”X∫Õ”ŒëÚ÷¯µƒ°∞«‡¥∫ÕØ–ƒ°±£¨À˚µƒ—€æ¶≤ª «ûÈ’J◊R ¿ΩÁ°¢∂¯ «ûÈå¢ ¿ΩÁ÷–µƒ“ª«–æ∞ŒÔ°∞‘Ÿ¨F°±ûȨçÀÈ∂¯–¬∆ʵƒâÙœÛ∂¯¥Ê‘⁄µƒ°£≤®µ¬»R†ñ’f£¨fl@∑N¬˛”Œ∞Y Ωµƒ°∞‘Ÿ¨F°±å¢Œ“ÇÉéߪÿµΩ…Ò‘í∞„µƒ°∞Õ؃Íïr¥˙°±£∫°∞É∫ÕØø¥ ≤√¥∂º «–¬ırµƒ£¨À˚øÇ «◊Ìı∏ı∏µƒ°£É∫ÕØ壖ƒ÷¬÷æ”⁄–Œ Ω∫Õ…´≤ ïrÀ˘∏–µΩµƒøÏò∑±» ≤√¥∂º∏¸œÒ»ÀÇÉÀ˘’fµƒÏ`∏–°£°≠°≠É∫ÕØ√Ê嶖¬∆Ê÷ƌԣ¨≤ª’ì ≤√¥£¨√Êø◊ªÚÔLæ∞£¨Ω≤≠£¨…´≤ £¨ÈW…´µƒ≤º£¨“¬÷¯÷Æ√¿µƒ˜»¡¶£¨À˘æfl”–µƒƒ«∑N÷±π¥π¥µƒ°¢“∞´F∞„≥ˆ…Òµƒƒøπ‚ë™‘ì «≥ˆ”⁄fl@∑N…ÓøÔ‰øϵƒ∫√∆Ê–ƒ°£°±(°∂≤®µ¬»R†ñ√¿åW’쌃flx°∑£¨π˘∫Í∞≤◊g£¨»À√ÒŒƒåW≥ˆ∞Ê…Á£¨1987ƒÍ∞Ê)◊˜ûÈÆîΩÒ◊Ó¡˜––µƒ«‡¥∫ŒƒªØ≈ºœÒ£¨÷‹Ω‹ÇêæÕìÌ”–fl@ò”“ªÎp∫¢Õتصƒ—€æ¶£¨‘⁄fl@Îp—€æ¶÷–£¨üo’ì…Ò√ÿµƒöv ∑ǘ’f°¢π≈¿œµƒÕØ‘í£¨flÄ «Æî¥˙…˙ªÓæ∞”^£¨∂º±ªèƒÀ¸Çɵƒïrø’’Zæ≥÷–∆∆ÀÈ≥ˆÅÌ£¨◊É≥…¡ÀÔh é‘⁄üo◊˘òÀµƒ–ŒœÛ ¿ΩÁµƒŒƒªØÀÈ∆¨°£÷‹Ω‹Çê—€÷–µƒ ¿ΩÁ£¨ «“ªÇĪÏÅyüo–Ú∂¯∆ÊÃÿüoœfiµƒ ¿ΩÁ£¨À˚”√À˚µƒá“’Z ΩµƒÕجïÔL∏Òµƒ∏Ë≥™å¢Œ“ÇÉ“˝»Îfl@ÇÄ ¿ΩÁ£¨◊匓ÇÉ‘⁄≈cüoïrÈgµƒÀÈ∆¨àDœÒ≥÷¿mµƒ“‚Õ‚≈ˆ◊≤÷Æ÷–œÌ ‹É∫ÕØ ΩµƒÛ@œ≤°£÷‹Ω‹Ç굃∏Ë£¨”–fl@é◊ÇÄ∏––‘Ãÿ¸c£∫‘~»±…ŸŒƒ“‚µƒflBÿû–‘£¨°∞«∞—‘≤ª¥Ó∫Û’Z°±£ª»´«˙üo’{–‘µƒî¢≥™’{≈cπ≈µ‰ „«Èò∑扵ƒÎsÙ€£ªµÕ√‘µƒâÙá“ Ωµƒ“˜≥™äAéß÷¯¡¡˚굃∏fl“Ù∏Ë≥™°£fl@∑N∏Ë«˙ÔL∏Ò£¨≤ªÉH «“ª∑N÷–Œ˜π≈ΩÒò∑ÔLµƒÀÈ∆¨ ΩµƒÎs∫œ£¨∂¯«“墓ª«–ø…∏–”X÷ÆŒÔ∂º◊É≥…¡ÀÉ∫ÕØ—€÷–µƒ°∞“‚Õ‚µƒÛ@œ≤°±°£(Ö¢“ä–§˙ó°∂«‡¥∫åè√¿ŒƒªØ’ì°™°™°™Îä◊”ïr¥˙µƒ°∞«‡¥∫°±œ˚ŸM°∑°∂÷–᯻À√Ò¥ÛåWåWàÛ°∑£¨2006ƒÍµ⁄4∆⁄)œ‡å¶”⁄«f◊”µƒ°∞ÃìÏo÷Æ–ƒ°±£¨÷‹Ω‹Ç굃 «°∞∏° é÷Æ–ƒ°±£ªœ‡å¶”⁄«f◊”µƒ°∞ò„Àÿ÷Æ√¿°±£¨÷‹Ω‹Ç굃 «°∞Ï≈ªÛ÷Æ√¿°±°£“Ú¥À£¨Ìn√¿¡÷’f“ªÇÄ’Ê’˝’JÕ¨«f◊”√¿åWµƒåW’fl≤ªï˛Õ¨ïr–¿Ÿp÷‹Ω‹Ç굃“Ùò∑£¨ «¿Ì‘⁄∆‰÷–µƒ°£
°°°°»Áπ˚æÕèV¡xµƒá¯åWªÚ÷–á¯Ç˜ΩyŒƒªØÅÌø¥£¨÷‹Ω‹Ç굃∏Ë≥™Àá–gÎm»ªÙ€∫œ¡À÷T∂‡Ç˜ΩyÀá–g‘™Àÿ£¨µ´≤¢õ]”–±Ì¨F≥ˆ‘⁄æ´…Ò…œ≈c÷–ᯌƒªØµƒ⁄ÖÕ¨ªÚå¶÷Æ◊˜∫ÍìP°£«f◊”’f£∫°∞∑Úµ¿≤ª”˚Îs£¨ÎsÑt∂‡£¨∂‡Ñtî_£¨î_Ñtën£¨ën∂¯≤ªæ»°£°±(°∂«f◊”°§»ÀÈg ¿°∑)≤ª™ö«f◊”º∞µ¿º“√¿åW£¨ø◊√œº∞»Âº“√¿åWÕ¨ò”◊∑«ÛÀá–gæ´…Òº∞∆‰±Ì¨FµƒºÉ¥‚–‘∫Õ“ª÷¬–‘°£‹˜◊”’f°∞æ˝◊”÷™∑Ú≤ª»´≤ª¥‚÷Æ≤ª◊„“‘ûÈ√¿“≤°±(°∂‹˜◊”°§ÑÒåW°∑)°£fl@∑N◊∑«Û°∞ºÉ¥‚ÕÍ»´°±µƒåè√¿¿ÌœÎ£¨åçÎH…œ « ¿ΩÁ∏˜√Ò◊ÂǘΩyŒƒªØµƒª˘±æåè√¿æ´…Ò°£÷‹Ω‹Ç굃∏Ë«˙◊˜∆∑£¨èƒ◊˜‘~£¨µΩ◊˜«˙£¨µΩ±Ì—›£¨∂º±Ì¨F≥ˆøÁïrø’°¢øÁµÿ”Ú∫ÕøÁŒƒªØµƒÎsÙ€¨FœÛ°£À˚µƒ‘~◊˜’fl∑ΩŒƒ…Ω£¨±ª√ΩÛw◊uûÈ°∞ÆîΩÒµ⁄“ª¥Û‘~»À°±°£»Áπ˚¥À’fÉH÷∏À˚µƒ∏Ë‘~Ñì◊˜÷–Ù€∫œ¡À‘S∂‡÷–á¯π≈µ‰‘ä‘~’ZÖR∫Õ“‚œÛ£¨ «ø…“‘≥…¡¢µƒ£ªµ´ «£¨»Áπ˚¥À’f÷∏À˚‘⁄Æî¥˙ŒƒªØ÷–ǘ≥–ªÚÑì–¬¡À÷–ᯑ~«˙Àá–g£¨Ñt≤ªƒ‹∑˛»À°£À˚µƒ‘~Ñì◊˜”–»˝ÇÄÃÿ¸c£∫µ⁄“ª£¨ëÚ∑¬Ã∆ÀŒ‘ä‘~÷–µƒÓjèU∏–Ç˚«È’{£ªµ⁄∂˛£¨ïrø’ÂeÅyµƒ“‚œÛ∂—∆ˆ£ªµ⁄»˝£¨ŒƒäA∞◊µƒ∑«flâ›ãµƒ’Z—‘ΩM∫œ°£°∂æ’ª®≈_°∑Æî埔⁄∑ΩŒƒ…Ω‘~◊˜÷–◊ÓΩ¸”⁄Ã∆ÀŒ‘~∏Ò’{µƒ“ª ◊∏Ë‘~°£°∂æ’ª®≈_°∑«∞É…∂Œ «£∫°∞ƒ„µƒúIπ‚»·»ı÷–éßÇ˚*ëK∞◊µƒ‘¬èùèùπ¥◊°fl^Õ˘*“πô¬˛ÈLƒ˝ΩY≥…¡ÀÀ™* «’l‘⁄Èwò«…œ±˘¿‰µÿΩ^Õ˚*”Í›p›pèó÷Ϻt…´µƒ¥∞*Œ““ª…˙‘⁄ºà…œ±ªÔL¥µÅy*âÙ‘⁄flh∑ΩªØ≥…“ªø|œ„*ÎSÔLÔh…¢ƒ„µƒƒ£ò”°£æ’ª®öàùMµÿÇ˚*ƒ„µƒ–¶»›“—∑∫¸S*ª®¬‰»ÀcŒ“–ƒ ¬ÏoÏoÃ…*±±ÔLÅy“πŒ¥—Î*ƒ„µƒ”∞◊”ºÙ≤ªî‡*ÕΩ¡ÙŒ“π¬ÜŒ‘⁄∫˛√Ê≥…Îp°£°±∆‰÷–£¨°∞ëK∞◊µƒ‘¬°±£¨≈c°∞”Í›p›pèó°±»Á∫Œœ‡≈‰£ø°∞ª®¬‰»Àc°±£¨”÷‘ıƒ‹°∞Œ“–ƒ ¬ÏoÏoÃ…°±£ø“‘Õıá¯æS‘u‘~µƒòÀú ’죨°∂æ’ª®≈_°∑º»Œ¥´@…Ò¿Ì(åëæ∞†ÓŒÔŒ¥ƒ‹’Êåçǘ…Ò)£¨”÷»±…Ÿºƒ≈d(≤ªƒ‹Ç˜fl_—‘Õ‚µƒæ´…Ò“‚Œ∂)£¨À¸Ωo”ˬ†±äµƒ÷ª «À∆ «∂¯∑«µƒ“‚æw∆Ø∏°£¨åçüoæ≥ΩÁø…—‘°£(¥À∏Ë‘~«È“‚≈cÀŒª’◊⁄⁄wŸ•µƒ°∂—‡…ΩÕ§°∑“ª‘~œ‡Ω¸À∆£¨µ´É…œ‡±»›^£¨æÕø……Ó∏–⁄wŸ•∏–ë—»À…˙”ŒÎxµƒ≥¡Õ¥∆‡≥˛µƒæ≥ΩÁ)
°°°°÷‹Ω‹Ç굃∏Ë£¨‘Æ”√ǘΩyŒƒªØ‘™Àÿ£¨’˝»Á∆‰‘Æ”√¡˜––ŒƒªØ‘™Àÿ£¨∆‰◊⁄÷º÷ª‘⁄ä ò∑£¨∆‰–ß”√“≤÷ª‘⁄ä ò∑°£À¸å¶”⁄ǘΩyŒƒªØµƒ“‚¡x£¨≤ª‘⁄∫ÍìP£¨∂¯ «œ˚Ω‚£¨“ÚûÈ‘⁄∆‰À∆ «∂¯∑«µƒ≈≤”√÷–£¨Ç˜ΩyŒƒªØµƒºÉ’˝–‘≈cÕÍ’˚–‘±ª÷´Ω‚∫Õ»°œ˚¡À°£ìQ—‘÷Æ£¨Ç˜ΩyŒƒªØ‘⁄÷‹Ω‹Ç굃∏Ë≥™Àá–g÷–£¨÷ª «“ª∑N±ª÷´Ω‚°¢∆¥ŸNµƒä ò∑‘™Àÿ°£”⁄µ§¬ï∑Q°∞Œ“’JûÈ÷‹Ω‹Çê∫Õ∑ΩŒƒ…Ω£¨ƒ≥∑N“‚¡x…œ£¨∏˙Œ“◊ˆµƒ ¬«È « ‚ÕæÕ¨öwµƒ°±£¨Œ“œ‡–≈”⁄µ§‘⁄¥À’f¡À“ªæ‰’Ê‘í£¨“ÚûÈÀ˝ π”√¡ÀÕ¨ò”µƒä ò∑ªØ‘≠Ñt∞—°∂’ì’Z°∑∫Õ°∂«f◊”°∑éß»ÎÆîΩÒ÷–᯵ƒ¥Û±ää ò∑ –àˆ°£Æ£¨À˝¬ï∑Q◊‘º∫≈cÀ˚ÇÉ «°∞ ‚ÕæÕ¨öw°±≤ªâÚ¥_«–£¨“ÚûÈ»˝»Àµƒ≤fl¬‘“ªò”°¢ºº«…“ªò”£¨≤ªÕ¨µƒ÷ª « π”√µƒ√ΩΩÈ≤ª“ªò”£∫∑ΩŒƒ…Ω π”√∏Ë‘~£¨÷‹Ω‹Çê π”√∏Ë≥™±Ì—›£¨”⁄µ§ π”√—›÷v’Z—‘°£ú ¥_÷v£¨‘⁄∞—ǘΩyŒƒªØä ò∑(”fiò∑)ªØµƒµ¿¬∑…œ£¨”⁄µ§÷ª «≤Ω÷‹Ω‹Ç굃∫Ûâm∂¯––’fl£¨À˝“‘÷‹Ω‹ÇêûÈ≈ºœÒ£¨µƒ¥_»Á∆‰◊∑≈ı’flÀ˘’f£¨ «”⁄µ§µƒ°∞’\åç°±µƒ±Ì¨F°£
-
----- ŒƒªØ–¬¬Ñæ´flx -----
- °§¿•«˙°∂ƒµµ§Õ§°∑¡¡œ‡ÒR∂˙À˚ ñ|Œ˜∑Ωπ≈¿œŒƒªØº§«È≈ˆ◊≤
- °§ÃΩ‘L°∂¨îº{Àπ°∑∑«ŒÔŸ|ŒƒªØflzÆaǘ≥–»À ÿ◊o√Ò◊Â÷«ª€
- °§“‘ǘ≤•…Áï˛åW“ïΩ«ÃΩÀ˜£∫–¬÷–á¯≈Æ–‘–ŒœÛ◊Éflw
- °§∆Ø—Ûfl^∫£µƒ°∞—Û√¿∫ÔÕı°±£∫∞—æ©Ñ°≥™Ωo ¿ΩÁ¬†
- °§Îp’Zœ‡¬ï≈c±ä≤ªÕ¨£∫Æ¬ï”ˆ…œ°∞Õ·π˚» °±
- °§Â\ıé°¢∑œµ°¢πŸ–˚...æWΩj¡˜––’Z≥…ŒƒªØ∑˚Ãñ
- °§π åmÕ∆≥ˆ°∞≥ı—©°±’{¡œπfi æW”—£∫èN∑ø÷±Ω”…˝ºâ”˘…≈∑ø
- °§µ⁄ Æ»˝å√¸Sµ€ŒƒªØá¯ÎH’ìâØ£∫åW’fl“‘‘ä∏Ë÷v ˆº“ᯫÈë—

- °§≤ª…·¬√∞ƒ¥Û–‹ÿàªÿᯣ°∞ƒ¥Û¿˚ÅÜå¢◊‚∆⁄—”ÈL5ƒÍ
- °§övïr3ƒÍøÁ‘Ω33ᯠ∫…Ãmƒ–◊”ÕÍ≥…ÎäÑ”‹á≠h«Ú÷Ƭ√
- °§∑¡_¿Ôfl_÷›á¯º“≤∂´@æfiÚ˛ ÈL∂»≥¨5√◊ÛwÉ»”–73Ówµ∞
- °§∏£‘≠ê€∆Ω∞≤Æaœ¬∂˛Ã• ¿œπ´Ω≠∫ÍΩ‹œ≤ïÒ“ªº“Àƒø⁄(àD)
- °§º”ƒ√¥Û“ª≤һƓÚï˛ÆãÆã◊flºt Æã◊˜“— €≥ˆ”‚231∑˘
- °§º””Õò匥 ’ÀæôCÒ{‹á∂¯»• º””Õ’æ…œ—›Û@ªÍÀ≤Èg
- °§∆Ø—Ûfl^∫£µƒ°∞—Û√¿∫ÔÕı°±£∫∞—æ©Ñ°≥™Ωo ¿ΩÁ¬†
- °§ƒzñ|¡“ ø¡Íà@»Îø⁄¿¨ª¯±Èµÿ°¢Õ£‹áÅy ’ŸM£øπŸ∑Ωªÿë™
- °§ΩYªÈ¬ ΩµÎxªÈ¬ …˝ «™ö¡¢“‚◊R·»∆flÄ «∑øÉrôŸF£ø
- °§æWºtƒÍ–Ω∞Ÿ»f£ø –àˆ’{≤È£∫ÉH20%µƒÓ^≤øæWºt‘⁄ŸçÂX
Œ“á¯åç ©∏flúÿ—aŸN’˛≤fl“—”–ƒÍÓ^¡À£¨µ´ «∂‡µÿòÀú “—͌¥ùq£¨∏flúÿΩÚŸN¬‰åç‘‚”ˆå¿fiŒ°£
- »’œµ∆˚‹á«∞∆flÇÄ‘¬‘⁄»A‰N¡øΩ¸200»f›v ƒÊ...
- °æàDøØ°ø„ë”õöv ∑ ƒ™Õ¸¿œ±¯
- °∞9.3°±¥ÛÈܱ¯»´¡˜≥Ã∆ÿπ‚ °∞πùƒøÜŒ°±…œ...
- á¯ÎH”ÕÉrÉ¥√Õ∑¥èó á¯É»∆˚≤Ò”ÕÉr∏Ò¡˘flBµ¯
- 30öqƒ–◊”ùMƒò∞ôºy»Á80öq¿œÓ^ „y––»°ÂX...
- ∞Ÿöqøπ»’¿œ±¯ Yƒ‹
- ∫”ƒœ500ÆÄ«fº⁄ ’´@‘⁄º¥±ªèäÁP »Œ–‘»«√Ò‘π
- °∞◊Ó±ØÇ˚◊˜Œƒ°±∞l≤º’fl“—ªÿº“ ∑Q÷ª «≈‰∫œ’{...
- ÷–ᯋá∆Û±»ÅܵœºÉÎäÑ”¥Û∞Õ¡¡œ‡∞ÕŒ˜ •±£¡_‹á’π
- °∞¨Fàˆ÷∏’J°±◊É°∞”ŒΩ÷ æ±ä°± œ”∑∏ô‡¿˚“™≤ª...
- «∞á¯ÎHäWŒØï˛÷˜œØÀ_ÒRÃm∆Ê ≈ ¿
- àD£∫∏flæ´º‚æØ”√Æa∆∑∫Õºº–g¡¡œ‡æ©≥«
- àD£∫äWŒØï˛…œµƒÀ_ÒRÃm∆Ê
- ”Òò‰µÿ’ûƒÖ^“ª“πÔL—© øπ’æ»ûƒ±∂º”∆DÎy(...
- àD£∫∏flæ´º‚æØ”√Æa∆∑∫Õºº–g¡¡œ‡æ©≥«(2)
- àD£∫∏flæ´º‚æØ”√Æa∆∑∫Õºº–g¡¡œ‡æ©≥«(3)
- àD£∫∏flæ´º‚æØ”√Æa∆∑∫Õºº–g¡¡œ‡æ©≥«(4)
- àD£∫∏flæ´º‚æØ”√Æa∆∑∫Õºº–g¡¡œ‡æ©≥«(5)
- àD£∫∏flæ´º‚æØ”√Æa∆∑∫Õºº–g¡¡œ‡æ©≥«(6)
- àD£∫∏flæ´º‚æØ”√Æa∆∑∫Õºº–g¡¡œ‡æ©≥«(7)
| „Ä?a href="/common/footer/intro.shtml" target="_blank">ÂÖ≥‰∫éÊà뉪¨„Ä?„Ä? About us „Ä? „Ä?a href="/common/footer/contact.shtml" target="_blank">ËÅîÁ≥ªÊà뉪¨„Ä?„Ä?a target="_blank">ÚqøÂëäÊúçÂä°„Ä?„Ä?a href="/common/footer/news-service.shtml" target="_blank">‰æõÁ®øÊúçÂä°„Ä?/span>-„Ä?a href="/common/footer/law.shtml" target="_blank">Ê≥ïÂæã£∞Êòé„Ä?„Ä?a target="_blank">ÊãõËÅò‰ø°ÊÅØ„Ä?„Ä?a href="/common/footer/sitemap.shtml" target="_blank">æ|ëÁ´ôÂú∞Âõæ„Ä?„Ä?a target="_blank">ÁïôË®ÄÂèçȶà„Ä?/td> |
|
Êú¨ÁΩëÁ´ôÊâÄÂàäËù≤‰ø°ÊÅØÂQå‰∏牪£Ë°®‰∏≠Êñ∞ΩCë÷íå‰∏≠Êñ∞æ|ëËßÇÁÇèVÄ?ÂàäÁî®Êú¨ÁΩëÁ´ôÁ®ø‰ª”ûºåÂä°Áªè‰π¶Èù¢ÊéàÊùÉ„Ä?/fo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