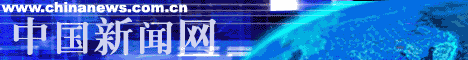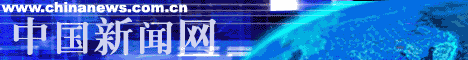提起殷承宗,總會和另一個名字聯系在一起——《黃河》。這位出生于鼓浪嶼的音樂少年,17歲的時候便在國際頂級水準的柴可夫斯基國際鋼琴比賽中奪得亞軍。在十年文革中,他讓鋼琴“洋為中用”,創作出鋼琴伴唱《紅燈記》而紅遍全國。為了還原鋼琴的真正藝術價值,他又創作出家喻戶曉的鋼琴協奏曲《黃河》。但是這位享譽海內外的鋼琴演奏家在文革結束之后卻遭遇事業的低潮,如今旅居美國的殷承宗精力充沛,每天與鋼琴為伴。
日前,殷承宗接受了鳳凰衛視《魯豫有約》的專訪。
魯豫:您現在每天練琴的時間大概是多少?
殷承宗:現在大概是五六小時吧,如果要學新的東西可能多一點。
魯豫:我注意到您的手,一般說彈鋼琴的手要特長,我看您的手也不是特別長。
殷承宗:我覺得彈琴,當然手是很主要的,但是腦子腦子和心更重要。現在有很多小手的鋼琴家,普尼列夫的手比我還小,但他的技術這么好。我的手小也會有一定的好處,我的手長得非常的勻稱,幾乎幾個手指一樣長,像一刀切一樣,而且我的無名指特別長,我的手比較寬,有力量。另外我的伸張力還挺好的,我以前彈不到十度,到40歲以后我十度能彈下去了,所以還是要靠練習,我現在每天還做這些伸張的活動練習。
年少的殷承宗曾經夢想和這些中央音樂學院的莘莘學子們一樣,接受專業的音樂培養,但是直到上中學以前,他都很少獲得接受正規音樂專業教育的機會。1954年,12歲的殷承宗在廈門市音協主席楊炳維的幫助下,只身前往上海,北上求學。
殷承宗:我媽媽一句話,我記得很清楚,她從小老說,你什么都要早,就是死不要早。所以那時我曾經為了練一個裝飾音、一個小節,練過八個小時。那天我說,我這個裝飾音要練不出來,今天不要睡覺,結果克服了這一次,很多東西一輩子都還在那里。
魯豫:那時候你在學校里的音樂目標是什么?你的理想?我想成為什么樣的音樂家?
殷承宗:那時候很簡單,我想去比賽,我想成為一個國際比賽獲獎者。那個年代比賽很少,有很多的機會。我那時候想到世界各國去演出,我很喜歡演出,那個時候就是這樣。
洋為中用
1958年,殷承宗便第一次實現了自己在國際舞臺上演出的夢想,四年后,他又在世界頂級水平的第二屆柴可夫斯基國際鋼琴比賽上,戰勝眾多強手奪得了第二名。然而中蘇兩國關系的惡化使他隨即中斷了在蘇聯的學習匆匆回國。1963年底,回國不久的殷承宗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見,并被鼓勵多創作一些民族化的作品。風華正茂的殷承宗滿懷激情,正準備大干一場的時候,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殷承宗順應“革命”形勢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殷誠忠。這時有人提出鋼琴是“資產階級的玩藝”,“不能為工農兵服務”,應該砸掉它。但殷承宗卻不愿看到鋼琴就此“滅亡”,他決心用實踐證明鋼琴可以“洋為中用”。
殷承宗:樂團派我們搞創作,我當時在廣播樂團,想用創作這種方法,寫紅衛兵鋼琴交響曲什么的,企圖想用一點京劇的曲調。我后來跟劉長瑜說,我試著寫幾段《紅燈記》你來唱。我當時很快,《紅燈記》前三段夜里寫出來的,第二天就找她來合,我覺得很融洽。我們在民族宮國慶節的時候演出,轟動得不得了,這樣就搞出來了。
1963年6月30日深夜,殷承宗得到中央領導的召見,被告知他創作的鋼琴伴唱《紅燈記》將作為建黨四十七周年的特別獻禮在全國廣播。當《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的位置報道了殷承宗在人民大會堂演奏鋼琴伴唱《紅燈記》的消息后,中國新聞電影制片廠又把它拍成電影在全國公映,殷承宗和他的作品一時紅遍全國。這一事件使鋼琴音樂在中國得到了史無前例的大普及,而與此同時,中國音樂學院鋼琴系的學生們則在為鋼琴在中國重獲新生彈冠相慶。
《黃河》協奏曲
鋼琴伴唱《紅燈記》獲得成功后,殷承宗開始考慮如何讓鋼琴從京劇伴唱的位置上獨立出來,使之突出鋼琴的地位和真正的藝術價值。殷承宗隨后和儲望華、盛禮洪組成三人創作小組,選定冼星海的《黃河大合唱》進行改編。
魯豫:在北京半年的創作過程中有沒有什么特別難忘的一件事情?
殷承宗:《黃河》的演出有幾次我要上臺的時候,都出了問題。第一次試演,突然我的中指指甲這發炎了,腫得很厲害。后來醫生讓我每天泡在灰錳氧水里頭,最后勉強包了手上去演出了。第二次就更嚴重了,“五一”正式演出,我彈《紅燈記》彈到最后一段的時候,在臺上腰扭了,整個動不了,站都站不起來了。只好關了幕把我抬下來,下個節目就要上《黃河》了,當時B組根本沒有人會彈,臨時決定《沙家浜》先上,把我拉到郵電醫院打麻藥,做了很多處理,最后拿繃帶把我的腰整個纏起來。
魯豫:能彈嗎?彈鋼琴動作很大的。
殷承宗:那個時候給我搞了一個有靠背的凳子,說如果不行的話,趕緊躺下去。但是我還是堅持下來,而且那場演出特別好!
魯豫:觀眾意識到了嗎?因為最后你都不能站起來鞠躬。
殷承宗:觀眾意識到了,觀眾也特別地熱烈,樂隊那天的合作出奇地好,所有人都盯著我,害怕我出事情,給我很大一個(信心)。但是黃河演出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二月份我們在小禮堂演出的時候。
魯豫:那個小禮堂?
殷承宗:就是人大小禮堂。那時候總理來審查,大家很激動,我記得保護黃河最后一段時候,把鼓皮都打破了。總理一直打拍子,最后他喊,是星海復活了,因為那個時候已經好久沒有聽冼星海的音樂了。
審查·赴美
1970年5月,鋼琴協奏曲《黃河》在北京的正式公演獲得了成功,這個作品也成為殷承宗日后到國外訪問演出的保留曲目。1973年,殷承宗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入黨后被提升為中央樂團領導。由于他在文藝工作上的突出貢獻,殷承宗還代表文藝界被選為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委員。然而四人幫的倒臺卻讓殷承宗的事業急轉直下,1976年,舉國上下開始歡慶文革大革命的結束,殷承宗卻被作為“中央樂團四人幫的代表”接受長達四年的審查。
魯豫:文革之后你接受了審查是吧?
殷承宗:對,大概四年時間沒有讓我上臺,不能回家,每天要寫很多材料。那段時間我覺得很渺茫,很痛苦的。
魯豫:還有碰到琴的機會嗎?
殷承宗:開始幾年我可以有,因為我坐在鋼琴前頭就會忘記一切。在完全不能回家的十個月里頭,我一是用腦子練琴,以前彈過的東西一條一條背。第二,我手小,就撐手,每天在桌子上劃道,今天撐到這兒,昨天撐到那兒。我天天夾著吃飯的筷子,不讓手縮回去。結果十個月出來以后,原來十度和弦彈不到的,手長大了都能彈下去了。
1979年審查結束后,經歷多年風雨坎坷的殷承宗有了到國外去重新奮斗的想法。1980年,殷承宗的夫人先于他以留學的身份到了美國,兩年以后,殷承宗攜同女兒也奔赴大洋彼岸。
初到美國,殷承宗的生活過得并不如意,這位享譽東方的鋼琴演奏家甚至為了能夠得到一架鋼琴被迫演奏自己不喜歡的樂曲。但是值得欣慰的是,殷承宗每天依然能以鋼琴為伴。在幾次個人獨奏音樂會后,美國的媒體開始關注起這位來自中國的鋼琴藝術家。殷承宗終于在這個西方的陌生國度里開辟出一片屬于自己的藝術天空。殷承宗現在經常自豪的說,他是目前仍然活躍在舞臺上年紀最大的中國鋼琴家。